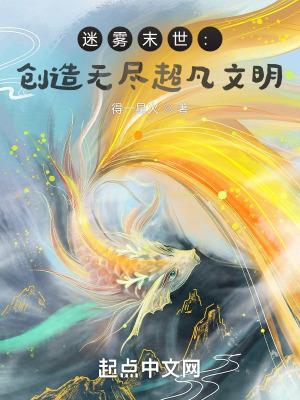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金钗凤 > 暧昧(第1页)
暧昧(第1页)
宴会在歌舞声中与朝臣百官的侃侃而谈中收场,宋琬草草与信王道别便摆驾回宫。
扶疏陪着在轿碾中,娓娓道来:“公主,奴婢方才打听了,信王姓贺名祯字行之,无父无母孤身一人投奔军营,十三岁入营,从兵卒升至大将军区区三载,战功显赫不骄不躁,在军营里有极好的名声。封为信王是去年的事儿,本是信郡王,后来擢升信亲王,一般便直呼信王。”
宋琬若有所思,只听扶疏继续说道:“信王私底下也极度自律,不入花楼,似乎,只有一位密友,是裴姑娘的嫡亲弟弟。”
“裴枫?”宋琬打断扶疏的话。
“是裴公子。”扶疏说道。
“说了半天,本宫听的囫囵。”宋琬道,“尽捡些没用的听。”话语中虽有不满,倒也不是真的恼了,扶疏忙住了口,乐得宋琬闭目养神。
——————————————
这头是主仆在议论,那头是兄弟在对话。他二人立在桥上,暗色的衣服融进夜里。
“信王今晚真是出其不意。”裴枫双手搭载桥墩上,看着池中鱼儿戏水,好不自在。
贺祯负手而立,片刻,他往池中砸了一颗细石,惊得鱼儿四处逃窜。
裴枫见惊扰了鱼,啧了一声,转过身靠在石桥上。
“我今晚瞧着,太女同你还未结发成夫妻,倒先琴瑟和鸣,好不般配。”裴枫调侃道。
“裴枫,你今晚怎么这么多话。”贺祯白了一眼裴枫,说道“皇帝虎视眈眈,我若是不顺着他的心愿,指不准明日便是杯酒释兵权。”
“魏朝蛮寇肆虐边境,满朝武将油嘴滑舌互相推诿,皇帝,在等你请战。”裴枫笑道,“他怎敢没收你的兵权。”
“后事如何,你我皆未可知。”贺祯道,“他想用区区太女拴住我,怎么可能。”
说完这句话,贺祯又往池中丢了一颗石子说道:“我非池中鱼。”
裴枫仰天笑的恣肆,拍了拍贺祯的肩说道:“忘了告诉你,别看太女一本正经,我听家姐说过,她好色。”裴枫贼兮兮说完这句话便离开,贺祯独自站在桥上,眼前闪过今晚宋琬的模样,有佯装镇定,有憨态可掬,有天家的尊贵,有……贺祯摇了摇头,低笑,他想她做什么,荒谬。
天上挂着的月亮被一团云隐约笼罩着,四更天了,宋琬宽衣洗漱后躺在床上,她回想起今晚贺祯身上特有的男子阳刚之气,她薅紧了被褥,沉沉睡去。
今夜,许多人各怀心思,直到白天宋琬起床才知道,昨晚她的好父皇临幸了一名宫女,已削了奴级抬为官女子。
宋琬不议,准备更衣临朝辅政。一席紫色官服傍身显得宋琬有些许老陈,宋琬蹙眉不甚满意这身朝服,差人去制衣局重新缝制,这几日便将就着。
朝野上下有许多宋琬不认得的面孔,听他们上奏,宋琬也分辨出了朝野上下的党派,宋琬面色微沉,等退了朝,皇帝唤宋琬进了御书房。
“娇娇今日有何见解。”皇帝一边批红一边问道。
“朝堂各党相互排挤,利弊参半,只此一日,儿臣不敢多言。”宋琬答的中规中矩。
“党派之争,历朝皆有,朕何尝不知道让他们相互掣肘以保朝中平衡。身为皇帝,这碗水既可适当摇晃,又要端平,别让水撒的见底。”皇帝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