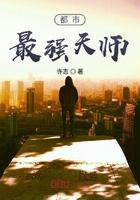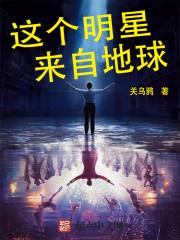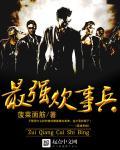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带着古人穿回现代 > 番外篇 算法中的莲蓉与分形(第1页)
番外篇 算法中的莲蓉与分形(第1页)
国家高等研究院,深层计算中心,A07实验室。
这里没有窗户,隔绝了日月流转。空气恒定在18。5摄氏度,湿度45%,只有高效空气循环系统发出几不可闻的白噪音。巨大的环形空间被冰冷的金属骨架分割,其上搭载着数台形态各异、闪烁着幽蓝或翠绿指示灯的超级计算阵列,如同沉默的金属巨兽,吞吐着无形的庞大数据洪流。空气里弥漫着臭氧、冷却液和精密仪器特有的、无机的金属气息。
实验室中央,一片相对空旷的区域。谢明哲盘膝坐在一张特制的、符合人体工学但毫无装饰的软垫上,背脊挺直,如同最精密的标尺。他鼻梁上架着特制的AR眼镜,镜片内投射出常人无法理解的、高速流动的抽象符号流和复杂多维结构模型。他的手指没有触碰任何实体键盘或控制器,而是在身前空气中快速、精准、恒定地做出点、划、抓取、旋转等手势。每一次手势,都引起AR视野中对应数据模型的剧烈变形、重组和推演。
他在重构一个理论模型的核心算法框架。目标:优化某种新型量子材料在极端环境下的能量逸散效率。冰冷的逻辑链条在思维中高速运转,排斥着一切冗余的感官干扰。世界,被压缩成了纯粹的信息流和数学关系。
突然。
实验室厚重的气密门无声滑开一条缝隙。一丝微弱却异常“顽固”的气息,如同投入绝对零度冰湖的一滴温水,穿透了精密的空气过滤系统,极其霸道地侵入了这片绝对理性的领域。
那是…甜润的、温软的、带着油脂芬芳的…莲蓉气息。混杂着新鲜麦芽蒸腾出的谷物清香,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竹制蒸笼的草木微涩。
谢明哲高速运行的手势,猛地停滞了一帧。
AR眼镜投射出的复杂符号流,如同遭遇了不可预知的引力扰动,出现了一个极其短暂、近乎无法被捕捉的微小“湍流”。
他极其缓慢地转过头。动作僵硬得如同生锈的机械臂。
门口站着他的助理研究员小唐,一个戴着黑框眼镜、总是带着一丝紧张和敬畏的年轻人。小唐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保温食盒,食盒盖子微微掀开,那股“入侵”气息的源头正肆无忌惮地弥漫出来。小唐脸上带着歉疚和不安,声音压得极低,生怕惊扰了实验室的“神灵”:
“谢…谢老师,抱歉打扰!是…是老夫人托人送来的,说…说是刚出锅的,务必让您趁热…呃…摄入。”他艰难地选择着词汇,不敢说“吃”,怕亵渎了这纯粹的科学圣殿。
谢明哲的目光,穿透了AR眼镜的虚拟光幕,落在了那个朴素的保温食盒上。镜片后的瞳孔,如同两个高速聚焦的精密镜头,瞬间捕捉到了食盒表面细微的水汽凝结形态、竹蒸笼特有的纤维纹理,以及从缝隙中逸散出的、代表特定分子运动的热红外成像轮廓。
祖母。
柳氏。
莲蓉包。
三个名词,如同三个输入参数,瞬间激活了他大脑中一个极其古老、却从未被删除的关联数据包。这个数据包,与冰冷的量子材料模型无关,却与某种被命名为“家”的混沌系统紧密相连。
他维持着盘坐的姿势,没有动。时间仿佛被拉长、扭曲。实验室恒定的白噪音似乎放大了无数倍,又似乎完全消失。只有那缕莲蓉的甜香,如同拥有实体的触手,固执地缠绕着他的感知神经末梢。
“放在…那边的…分析台上。”谢明哲开口,声音依旧是那种缺乏起伏的平直电子音,但音节之间,似乎多了一帧极其微妙的停顿。他指向实验室角落一张冰冷的、通常用于放置待测样本的金属台面。
“啊?哦!好!好的!”小唐如蒙大赦,赶紧小跑过去,将保温食盒小心翼翼地放在光洁的金属台面上,仿佛在安放一枚易碎的文物。他不敢多留一秒,迅速退了出去,气密门无声合拢,再次隔绝内外。
实验室恢复了绝对的寂静与“纯净”。只有超级计算机阵列散热风扇的低鸣,以及…那缕顽强存在的莲蓉甜香。
谢明哲没有立刻回到他的量子模型。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微微侧头的姿势,AR眼镜的镜片对着角落的金属台。无形的思维触角,却已从浩渺的量子海洋中收回,聚焦在那方寸之间。
他站起身,动作依旧带着一种精确的机械感,走向金属台。AR眼镜的视野里,保温食盒被迅速分解、建模:外壳材料(食品级PP塑料,保温层厚度5mm),热源中心(温度约62。3℃,基于红外成像),内部空间结构(基于热传导模型反推),内容物形态(圆形,直径约6。5cm,高度约3。2cm,表面存在细微褶皱,符合“莲蓉包”形态特征)……
数据流在眼前瀑布般刷过。但这一次,他大脑核心的运算模块,却并未全力处理这些物理参数。一个更“低效”、更“冗余”的次级进程被强制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