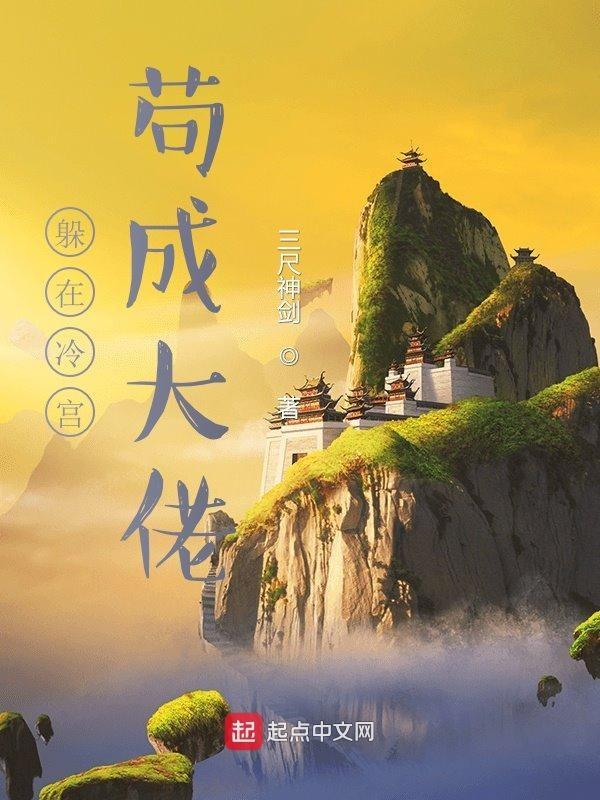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春情暖 > 第 68 章(第2页)
第 68 章(第2页)
何逸之应了一声,立刻挤到几个抬酒工中间,合力抬起一个酒缸。甫一上手,他心里便是一惊,这缸的重量远超想象,绝非寻常装满酒的缸该有的分量,沉甸甸得像是灌满了铁砂。
他一边使力稳住身形,一边故意装作吃力地喘着粗气,对旁边一个皮肤黝黑的老抬酒工搭话:“老哥,这玉家的缸可真他娘的重!怪不得工钱给得高,这活计一般人还真干不了。”
得亏何逸之前些年独自跑出去“混江湖”,接触不少寻常百姓,这粗话也是信手捏来,倒不显得自己突兀。
那老抬酒工也是累得够呛,抹了把汗,咧嘴道:“谁说不是呢!小玉东家仗义啊!就因为这缸大、缸重,比别家抬一缸费老鼻子劲了,所以工钱才给这个数!”
他伸出五根手指比划了一下,脸上带着一丝满足,“比别家多半数呢!虽然累点,但值!”
何逸之装作恍然大悟,又带着点好奇,“光缸就这么沉?那里面装的酒岂不是更多?难怪玉家的酒卖得贵。”
“嘿,谁知道呢!反正东家交代了,只管抬稳当,别磕着碰着,里头装的是琼浆玉液还是别的啥,咱可管不着。”另一个年轻点的抬酒工插嘴道,语气里带着点谨慎,似乎不愿多谈。
何逸之心中疑窦更深,这重量分明不对,缸壁过厚,抬酒工也是语焉不详。
但他没再多问,只是埋头干活,默默记下车队行进的方向。
车队终于抵达了城门时已日暮西山,可何逸之观察这些人似乎并不准备停留,要连夜将酒缸送出关外。
工头将工钱分发到每个人手中,何逸之掂量着手中明显超出常例的工钱,更加确信这“重金”背后必有蹊跷。
他随着众人散去,悄无声息地绕到一处阴影处,盯着不远处的牛车。
何逸之锁定一辆装着最大号酒缸的牛车。
屏住呼吸,看准一个守卫背过身去的瞬间,随手捡来起一枚小石子,灌注巧劲,精准地弹射在拉车那头老黄牛的后腿关节上。
“哞——!”老牛吃痛受惊,猛地向前一窜!沉重的车身随之剧烈晃动。
那个被巨大酒缸本就因牛的突然发力而重心不稳,加上缸身异常沉重,瞬间从车架上翻滚下来!
“轰隆——哗啦——!”
一声沉闷的巨响伴随着刺耳的碎裂声,硕大的酒缸重重砸在地上,瞬间四分五裂!
何逸之眯着眼,本该浓郁酒香四溢、酒液横流的场面并未出现。
破碎的厚实缸壁内侧,赫然露出一个夹层隔断,隔层之内,暮色微光映照下,何逸之看到了一柄柄打磨得锃亮的崭新刀身!旁边还塞着几捆同样用油布包裹的枪头!
“糟了!缸破了!”“快来人啊!”护卫的惊呼声和杂乱的脚步声开始变多。
何逸之心脏狂跳,但头脑异常清醒。
他飞快地扫了一眼那些藏得严实的兵器,又瞥了一眼惊恐奔来的守卫脸上异常的戒备狠厉。
“假运酒真运兵刃!玉家好大的胆子!”这个念头如同惊雷般在他脑中炸响。
他稳住气息,静观其变。
大批量兵器无通行令,不可随意进出任一城邑。
方才锦州城门上的守卫听到动静快步跑来,何逸之确定他们看见了缸中的兵器,却神色平常,吩咐人加快收拾,处理很熟练。
‘孙辛树知晓并默许玉家行此事,要赶紧回去告诉表兄。’何逸之借着夜色没入深巷,转眼消失。
闻栖鹤听完何逸之查到的消息,指尖在桌沿轻轻敲击了两下,薄唇微启:“原来如此。”
假借向关外富商运酒作为他们往外输送兵器的幌子。
他抬眼看向何逸之,那双眸此刻深不见底:“可有看清制式?”
“刀是军中常见的朴刀样式,枪头也是制式长枪头,打磨精良,簇新。仅破开那一缸,夹层内藏刀身约十柄,枪头二十余枚。观其车队规模与缸体大小,这一批……怕不下数百!”
李红杏倒吸一口凉气,难以置信:“私运如此大批军械,锦州太守的人都没发现过吗?”
“怕不是没注意,而是明知暗保。”
“确实如表兄所言,锦州城门守卫对玉家用大缸运送兵器一事处理娴熟,显然习以为常。”
正当几人密谈,孟贺来了,面色沉重:“情况不妙,已有人盯上我们,孙辛树估计有所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