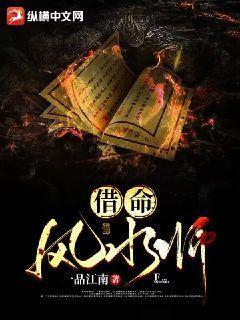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逃出人贩窝 > 第42章(第2页)
第42章(第2页)
“再说了,现在那骗人的可是不少,要是我带着她上你家,说给你做媳妇,你信不信?”老头看了看周围,继续说道:“咱这个山沟沟里出生的人,讲究的就是实在,把女人捆上了,不管是卖的还是买的,都心里觉得踏实,也不用让人觉得受了骗似的,大伙说对不对?”
一番话说得周围人都哄笑了起来,那人也嘿嘿地傻笑着。
本来这个街上只要一有女人被捆了来买卖,便有好多人过来围观,大人小孩看的人多,也有那女人在边上指指点点的,或帮着自家还未成亲的男人看看货,也有给远处的亲戚家说个亲的,自然总有女人在这里成交。
有那看了谭韵身子动心的人,一问价钱都撇了撇嘴摇着脑袋,这村里也有很多的光棍,不过都是穷得叮当响的人,看过在这里被卖出的女人也不少了,可眼前这个身材儿如此窈窕的女人,倒还是很少见,如今就捆在他们面前,却兜里没钱买不起,心里也实在痒痒得很。
好几个想看看谭韵脸蛋的,都被老头拒绝了,他要看准了那个愿意出价的才会给他看那脸盘儿,到时候便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买主也能有个定心丸。
老头一直巴望着能卖个好价钱,可他的开价也太高了些,几个外村带着那心思来逛街的男子,问了价钱也不敢再回答,看了好一会才依依不舍地走了。
眼看着将近黄昏了,街上的摊子也越来越少,原先在一边那棵碗口粗的树干上,捆了的两个女子也早让人买走了,那两男一女三个卖主,也数着钱悄然地离开了。
围观的人渐渐离去,就有些孩子还在附近闹腾着,老头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便想着要是再有一个人想要买的话,就把价钱降低一些,总比卖不出手再带回家要好。
其实在不远处,早有一对父子一直在看着他们,眼看着老头心急的样子,此刻便走了过来,那个五十多岁的做父亲的蹲下身子,也不问价钱,对老头说道:“看看货,好的话,就出个价。”
老头一看就知道有门,大概是那做爹的给儿子买媳妇,看那样子应该是有钱的主,便赶紧把谭韵的花布衫解开了,裸露出那五花大绑着的身子,又摘下了谭韵眼睛上的黑布。
谭韵被突如其来的光亮刺的眼前直晃,便闭了眼睛,可那闭着眼睛的样子,也让那对父子眼前一亮,知道是个好货色,尤其那身子更是诱人得很,周围看的人中,能动心的都不由自主的身子起了反应。
父子两不再多说,掏出一叠钱来丢在老头面前:“就这个数,愿意的话就成交,不愿意那就算了。”
老头拿起来数了数,比他心里的估算要少了两成,本想再还还价,但看那对父子似乎铁定了心就是这个价钱,倒也不能再开口,便将钱揣好,把谭韵交给了他们。
那个做儿子的,一直没有说话,此刻把谭韵往肩上一抗,跟着他父亲就走,也不管她衣衫是否滑落,一路轻松地就到了一条河边。
河上停了一条不算小的木船,似乎是专门替人运货的,一块跳板从船帮搭到了岸上,父子两人晃晃悠悠地就上了船。
船舱很宽敞,进去后,谭韵便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姑娘,同样也被捆绑着身子,嘴里塞着毛巾,眼睛上还覆盖着棉花,用布条子绑的严严的,人斜坐着倚在舱壁上,看起来受了很大的委屈,因为那几乎赤裸的身子上还有几条血痕,好像是被鞭子抽打的。
谭韵一看这情景,心里便开始发毛了,她哪里知道,这条船的主人竟然是放鹰的,也就是把女人放出去作钓饵,找个富有些的男人嫁给他,到时候再收回来,专门劫夺有钱男人家的财物,这种事解放前就特别的多,解放后就基本绝迹了,哪知道如今又开始泛滥起来,尤其是在这样偏僻不发达的地区。
船上还有个中年女人,一看就知道父子两人和那女人是一家子,估计干这行也干了好多年了,一幅精明的样子。
上了这条船,可就要按照他们的规矩来了,整整一个多星期,他们每天都要把她揍一顿,然后教给她一些规矩,要她牢牢记住。
晚上,那个叫阿明的儿子,便会毫无顾忌地当着他父母的面,和她睡在一个被窝里,而那个被捆绑的女子,就在谭韵上船后的第二天一早就被阿明的母亲带走了。
父子两人在船上经常地威吓她,谭韵每天都是泪水满面,慑于他们的威胁,不敢叫也不敢哭,哪里还能有所违抗,他们教给她的那些行事的规矩,在他们的威逼下记得熟熟的,并且还逼她说出自己家的住址,同样又是威胁她,马上就可以查到她说的是不是假话,如果是假的,就把她沉入河底。
这谭韵一开始还真的编了个假地址,再一听他们要去核实,心里就慌了,赶紧讨饶着抖抖地说了出来,内心祈祷着家里的父母千万不要遭受这些人的报复,自然也不敢再有违背他们意愿的心思。
船儿一直就在河道中行驶着,也不知到了哪个地段,谭韵从没有出过舱来,始终被捆绑着堵上嘴关在舱内,为怕她把路途记在心中,除了吃喝便用布条绑着压住眼睛的棉花,不让一点光亮给她看到。
阿明来了兴致想起要她时,就会在舱里随意的蹂躏她,晚上,他的父亲也会睡在一个舱内,没过几天母亲也回来了,即使老夫妻想干那事也不避讳儿子和谭韵,似乎船上人的生活向来都是如此。
船又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有女人来报信,说是有生意来了,谭韵虽然被蒙着眼睛看不见,但能听见他们说话,心里越发的害怕,知道他们不光光是一家子,居然还有很多他们的亲戚一起干着这事,心里便绝望起来。
傍晚时分,船摇晃了几下,谭韵知道有人上船来了,低矮的舱门打开时,便听到了一个女人“呜呜”的叫声,随即那女人被推得躺倒在了舱板上,阿明的爹似乎在查看女人带回来的东西,嘴里骂骂咧咧的:“臭女人,就这几样东西?他们家不是很有钱么?”
谭韵知道这一定又是哪个女人,被放了鹰,现在收回来了,可能带回的东西不多,被他们责骂着,女人嘴里的布团被取了出来,十分害怕地哭泣着:“他……他们家……本来就没钱……以前,那都是跟别人借的……”
“啪……”一个耳光打在了女人的脸上,男子骂道:“还敢嘴硬,老子把你送去的时候,他们家不是搞得排场很大么……一定是你舍不得那男人了,是不是?”
“不是……呜……呜……”女人哭了起来,但随后又被毛巾塞住了嘴,那哭声便被压抑在了嗓子里。
晚上,谭韵就被带上了岸,浑身被捆绑的结结实实,嘴里严严地堵塞了棉布,还绑了一只口罩,眼睛上压着厚厚的棉布,用白布带子缠绑得很严实,一路上趔趔趄趄地被那老夫妻两人挟持着,走了好一段路便来到了一户人家。
听他们打招呼,便知道这又是那夫妻两人的亲戚,而且还是个长辈,,他们的谈话并没有避开谭韵,大致的就是已经找到了人家,听说那家的男子是个暴发户,前段时间还是个穷得一塌糊涂的光棍,不知怎么的居然突然有钱了,便找人四处打听有没有漂亮女人给他介绍一个。
这消息便溜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经过几番的安排,又有那受了钱财的媒婆上门说亲,决定找个地方见次面,要是满意的话立刻就可以结婚办喜事,男方那边因为早就死了父母,所以一切都由自己作主,这边女方这里,自然都在他们的安排中。
于是,半夜里,他们就给谭韵松了捆绑,将她关在一个房间里独自睡下,睡觉前,几个人又是恐吓,又是好言相说,把明天要办的事都跟她说了,一句话就是要她好好配合,别到时候出了岔子,那就没她的好果子吃,还要连累她的父母。
谭韵知道厉害,十分顺从地都记在了心里。
这一晚,她几乎没有睡着,虽然身子没有被捆绑,但内心的紧张和恐惧让她辗转反侧,还冒出偷偷逃跑的念头,但这些天来的折磨让她生生地对他们产生了恐惧,那些逃跑的念头一闪便消失了。
第二天一早就被他们叫了起来,身上的那些绳痕都已褪去,滑嫩的把胳膊和身子,自然不是乡下女人所能有的。
阿明他娘拿出了几件女人的内衣,给谭韵穿上,可尺寸小了些,胸罩几乎把那对丰满的胸乳箍得要撑破似的,三角裤也无法提上那丰腴的臀部,仅仅遮住一点点的三角部位,黑黑的还有一半露在外面,他们可不管了,又忙着让她穿上衬衣和裙子,总算给她打扮得像个姑娘似的,虽然有些土气,倒也没有掩住谭韵的天生丽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