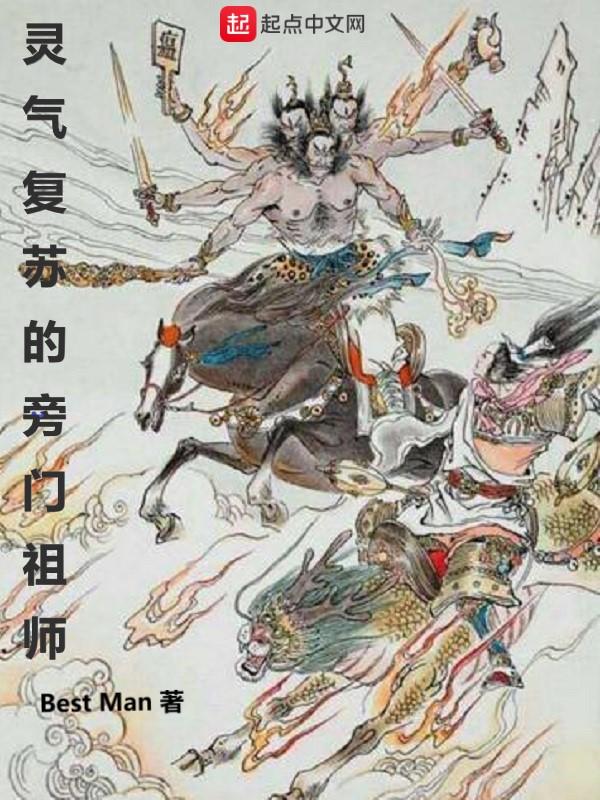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合魂记 > 第209章(第2页)
第209章(第2页)
“现在还没有,只是我的姑姑一向很警觉,天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怀疑了。”
其实我鼓励梅老师享受自己,多少带点恶意,因为前世特别厌恶官僚,今世还是如此,虽然知道随着长大,我会逐渐改变,但在改变前,我总想鼓动官员太太,给自己不安分的老公多带几顶绿帽子。
“嗤!”梅老师放下心来,可突然,又脸色大变,说,“你不会已经厌烦梅老师了?想换口味了?”
“唉!梅老师,你把我想得太坏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啊,这个小白痴想勾引程立雪了,是吧?你放心,我做过的承诺,决不会食言。”
梅老师脸色才慢慢好转,她伸手抚摸着我的脸,有点忧伤地说,“原来啊,担心被人发现,丢人。现在呢,觉得也许有一天,会为你伤心了。”
梅老师话里的真诚让我感动,可我不知道该如何接口,我现在不敢随便做什么保证了。
我又赶紧转换话题道,“梅老师,你结婚近十年了吧,怎么就没有孩子呢?”
“怀不上啊,怀上过几次,也都流掉了。”话里更加伤感了。
我突然心中一动,“梅老师,那你从来不用安全措施的?”
“怀都怀不上,还用什么措施。”梅老师的脸略略有点红。
我本来一直埋首于梅老师的胸口,边抚弄,边和梅老师聊天,此刻我一跃而起,有点慌乱地说,“那你可能怀上我的孩子?”
梅老师的脸更红了,声音低低地说,“你不会怀疑梅老师为了借种,有意勾引你吧。”
我苦笑着说,“借种我倒无所谓,只是我家情况特殊,你要生个儿子,就要去做亲子鉴定,看看是谁的儿子了。”
“胡说!我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梅老师有点生气。
“我家几百年来,多世单传,族人深信不疑,对这个儿子都看得极重,我倒是身不由己啊。”
“什么身不由己,”梅老师气急败坏地说,“我不管你家几世单传,也不管你家有多少亿资产,我才不会让我孩子去做亲子鉴定,我宁可杀了你这小白痴!”
我呆呆看着梅老师,突然恍然大悟,“是啊,我干吗要在乎这个,我又不是白痴,我干吗要在乎是儿子还是女儿继承财产?”
想通了,我大笑着开玩笑,“是啊,我干吗管这么多?我这辈子大概会很风流,可能会在不少人肚里下种,等我临死,一纸通告,凡是可能是我孩子的,都来做亲子鉴定,分几千亿财产,也许你儿子会第一个来呢。”
“滚你的蛋。”梅老师笑骂我。
“滚我的蛋就免了,你还是摸摸我的蛋倒好,我们就可以继续耕耘,努力下种。”
说着,我的手又游走于峰峦溪谷,梅老师推拒着说,“今天算了,还是细水长流吧。”
“好啊,我们就细水长流。”手却不停。
“那还不老老实实?还乱动?”
我笑嘻嘻地说,“你不是说细水长流吗,我们就要‘经常’流一流啊。”
“你瞎解,是这个意思吗?”梅老师有点疑惑。
“梅老师,我不是嘲笑你们英语老师,你们英语老师啊,现在除了会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啊,文学都一窍不通,怎么学得好语言?汉语一窍不通,怎么学得好英语?--当然,我说的是徐老师这类英语老师,你梅老师另当别类。”
我看梅老师的脸色有点不好看,赶紧笑着补充。
梅老师叹气道,“你也有资格嘲笑,谁叫你是语文天才呢。”
我语文作业从来不做,上课从来不听,但考试总在年级数一数二,师生都已认可我是语文天才了。
玩笑开完,兴致上来,这回梅老师闭着眼睛,随我折腾。
把梅老师弄得趴伏,上身低伏,雪臀高耸,揉着分开,暗褐色的后庭新鲜娇嫩,手指轻触,梅老师抗拒地躲避,“不要。”
口气生硬,听来不高兴。
是啊,答应下种,怎么采花了呢?
我就下种,犁头插到底,开始耕耘,听着雪白山峰传来奇妙的撞击回响,看着雪浪一波一波漾开,我兴发如狂,奋力冲击,心底也隐隐感觉到,似乎在梅老师的子宫深处,有个微细的梅老师,正在含笑向我招手,等待着和我牵手。
于是我更深入地进入,紧紧抵住深处那似骨非骨的奇妙,喷涌下种,我确信,我这次下种成功,一定会收获一朵花。
同时我心里也暗暗想着,等她肚子充盈,以保护孩子为由,我会让她用后庭为我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