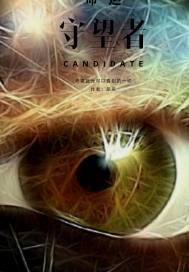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乌孙悲欢 > 第3章 翁归(第4页)
第3章 翁归(第4页)
某次闲谈时,翁归告诉解忧,乌孙旧俗,昆弥要哪个儿子接位,就给名字后边加一个带尊号意味的“靡”,以示王储身份:“所以左夫人生的,我起名乌就屠。”见丈夫暗示不愿匈人血统的儿子接位,却并不解释,解忧也不追问,只在心底留一个问号。
当她给丈夫生下第一个儿子,想取汉名“元贵”,元为首,含“一等贵胄”之意,翁归貌似随意的说“合适的时候,就叫元贵靡吧!”
解忧一时欢喜难以自抑,不由问起为何丈夫不愿匈人血统的子嗣接位?
翁归脱口而出:“草原的鹰,是不能听命于远方的!”
解忧失笑道:“我却是中原的小雀儿,陪伴你这大鸟,吃力的紧。”翁归也笑了:“长生天助我化身为羊,你落在我背上睡大觉可好?”夫妻痴笑不止,却有了个不再提起的默契:“将来,我们的儿子也是昆弥。”顺便,两人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军须昆弥的儿子,与王座无关了。”
************
在翁归时代,赤谷城盛极一时。
全西域的贵人都交汇于这座急速改变面貌的大都邑。
在公开交际的场合,解忧尽己所能,不让任何人感觉受了昆弥汉夫人的冷落。
她似乎天生擅长捕捉每个人暗含于心的一念一动,不动声色化解于无形。
也许只有泥靡母子的怨毒是个例外,但泥靡本就是她命里的魔星,是无从抗拒的厄运……
当翁归猝然离世后,儿孙满堂后的解忧遇到了命里的魔星,逃不开,躲不及。
更可怕的是,她犹豫过后,主动拥抱自己的厄运。
也难怪泥靡翻来覆去地念叨汉家女是如何天生下贱……
经过了与翁归近三十年的美满日子,解忧以极快的速度投入新的生活,适应新的男人,寻求新的生存。
在一个彻底漆黑不见五指的情欲王国里,“乌孙国母”有智慧和见识,泥靡昆弥有鸡巴,还有两个叮当乱响的卵蛋。
最后的赢家是谁?
无论谁赢,汉家公主注定要在这场肮脏游戏里变得满身污秽。
解忧暗暗决心,让“圣主”离不开自己,无论在乌孙的王座上,还是在情欲王国的罗网中。
话说回来,无论小男人如何气急败坏,解忧从不肯做如此露骨告白:
“是的,翁归夫人很风光,但她更渴望当泥靡的奴隶。”“是的,翁归是乌孙的英雄,但泥靡是神圣的主人。”
永远只有默认、暗示、略带反感的提醒,娇笑着却又目带责备,似乎说“我的圣主,国母在你的鞭打下很快乐,很快乐……可你为什么不理解?我是不能说出口的!”
泥靡的报复是凶残的,他玩不转“笑中有泪”“悲中带喜”的小儿女调调儿,他甚至接受不了中年夫妻的平淡默契。
解忧为什么还要坚持?
或许,恰好是这个搞不懂的调调,吸引着愚鲁的小男人,刺激着他的本能。
翁归跟她试过几次肛交,她不喜欢!
饶是汉子如何讲道理,老婆不喜欢!
汉子一脸苦相:多少娘们都干过的……时移势转,泥靡喜好折磨国母的后臀,阳具搅动带起的痛楚让女人辗转挣扎,巴不得死掉……可每隔数天,汉家女总免不了轻怒薄怨地提醒泥靡,国母的肠道温热如旧,何姗姗来迟?
有时泥靡换一个洞来玩,刺激的女人情欲泛滥,却又铁枷一般锁住产道的扩张与收缩,猫玩老鼠一般戏弄的她发了狂,哭着乞求给国母一个高潮……恢复尊严后,老女人却不吝于大胆戏谑,说什么昆弥只是“小主人”,昆弥的独眼兄弟才是“大主人”。
“小主人”的意志,国母固然服从,“大主人”要国母的命,国母却也不敢不给的……大胆的戏谑,换来的自然是加倍的羞辱……
无论泥靡的欲望如何焚烧她,汉家女人总能浴火重生。
她仍是乌孙人拜服的国母,光彩四溢。
在解忧的辅佐下,乌孙一度的混乱渐次平息。
西域诸小国又开始买乌孙昆弥的账,泥靡却趁机把情欲张扬的更加过分,陆续攫取了多位西域王族女性,或收继为妾室,或干脆“恩赏”了奴籍。
她们中有贤名远播的王太后,年纪比解忧还大;有才貌双全、正值盛年的王后;有青春正炽的小姑娘,也有初尝家庭甜蜜的少妇……但“鸡巴昆弥”(冯嫽私下给泥靡起的诨号)仍死死缠住国母不放。
或许,他需要解忧的辅佐之才,更或许,他深深的迷恋着国母的受虐癖,即便是那狡黠的汉家老骚儿演出来的,也演得可算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