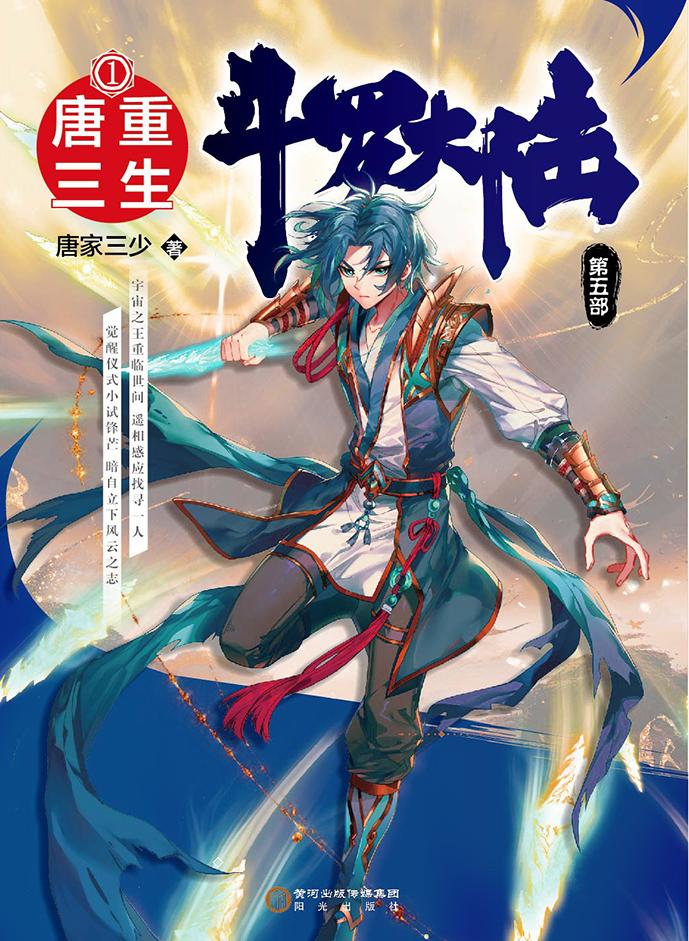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江山云罗 > 第13章 独退雄兵 念不宜多(第2页)
第13章 独退雄兵 念不宜多(第2页)
希望梦幻泡影般破碎,谭安德再也坐不住,先派了两只万人队出城,携带五天的口粮护送一批船只出城。
嘱咐无论如何要护住这批粮草,至于他们的口粮,五日之内自然会另由后军送来。
两队的将军们大喜过望,州牧大人这是毫无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能送一次算一次。
好事落到了自己头上,这批粮草能送到葬天江边,罪责能减轻多少?
若是后续再也不能运送出粮草,自己这一趟还是大功一件!
两支万人队兴冲冲地出了城,运送粮草去了。
人多胆气就壮,一路上陷阵营也的确不敢来与这只大军正面交锋。
或许这帮匪徒想的是等大军回城之后再动手,可惜啊,州牧大人神机妙算,大军不会回城!
次日一早,又有两只万人大军先后出城,显然是给前面运送粮草的大军送给养去的。
两万人的大军,要运送给另外两万人马的给养,加上自己要吃要喝的,队伍如长龙,足足走了半日才出了城,迤逦一路向南而去。
以巨大损耗的代价,徐州终于送出去一船队的粮草。
但徐州官员们依然忧心忡忡,转眼去了四万大军,徐州剩下的三万军马只够守护四处郡城之用,甚至徐州城里都只有一万军。
如此一来,在护粮大军回来之前,接下来的日子是一颗粮食都不用想运送了。
然而时值夜半,还是出了事!
一小队十余人的小军星夜赶回徐州城在城外叫门,守城军认得是今晨派出去的兵丁,赶紧放下吊桥。
那队小军入了城就开始大哭祸事了祸事了,要立刻面见州牧。
谭安德一问,登时面如死灰。
原来今日出城给护粮队运送粮草的大军刚刚扎营不久,统兵将领召集诸将在大帐里商议,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十几名细作居然混在大营里,见面三下五除二就剁翻了几名将领,把尖刀架在大将的脖子上。
领头的是一名女子,风姿之美令人不敢逼视,也不知道她在大帐里说了些什么,诸将就此投降,大军拐道,押着粮草补给向陷阵营驻地去了。
他们这队小军趁着夜色逃脱,星夜赶回报信……
谭安德一副大限已到的样子软倒在椅子上,好半晌才有气无力地道:“去召集上下官吏,本官有事要商议。”
长史,治中,别驾,功曹,还有一众将军得了信,火速赶到州牧府。
只见谭安德在窗前怔怔望天,谁也不理,边上除了个面生的小厮手里捧着圣旨,再无他人。
一州官吏将军挤得厅堂满满当当,人都到齐之后,谭安德才回过神来,从小厮手中接过圣旨展开,又怔怔地看了半天,随手递给长史道:“事情都知道了,你们看,怎么办吧……”
厅堂里静得只余丁点呼吸声,仿佛一众官员的呼吸都快停止,圣旨从头传到尾,人人头顶冒汗,没有人说一个字。
“大人,不若……山穷水尽,为今之计,不若……不若……”
“不若什么?”谭安德目中寒光一闪,好像抓住救命稻草大声逼问。
“下官以为……不若……降了吧……或有一线生机……”
“降?”谭安德大吃一惊,向后连退两步,砰地一声撞在桌案上,道:“为何要降?”
说话的长史把心一横,转身对官员道:“诸位!且听我一言!”
“你说!”谭安德咬牙切齿,他一发话,此刻暂时无人敢跳出来反对。其实到了眼下这个地步,人人自危,但有一线生机,谁又不想听一听?
“陛下,陛下……”长史的牙齿咯咯噔噔,艰难道:“陛下在长安连吴征都擒不住,当真是……当真是……我知道吴征神通广大,但是让他逃了出来无论如何说不过去。陛下不仅不自思其过,还将罪责全数抛给他人,非明主也!泗水受阻,朝中没有反制之方就逼迫我们,事还未办,旨意先到!近日来,诸位谁不是殚精竭虑?力所不能及,又有何法?谁能心服?我第一个不服!主不能善待臣属,臣属又何须忠于主?陛下自己无能,放吴征龙归大海,事后怪罪下来,责任全是在座诸位,我们成了国家罪人,一辈子翻不了身!凭什么?”
“反了……徐州孤城一座,届时大军围剿,我们死无葬身之地……”治中听得胆战心惊,颤抖着道。
“可以守城,守得住……”别驾也豁出去似的站起,大声道:“陷阵营于野战中尚能杀得各路大军肝胆俱裂,看看平虏军!他们同样无路可走,就以徐州坚城为依托,怕得谁来?”
“你且详细说说!”谭安德眯了眯眼,似乎已被说动。
“竟敢大逆不道!大人,切莫听这帮逆贼妖言惑众,就算陛下责罚,也绝无……”
一名将军抽出腰刀,就要斩下长史的人头,却忽然悄无声息地倒在地上,喉间鲜血狂喷,身体抽了两抽就不再动了。
谭安德身边的小厮抹了抹带血的尖刀,道:“大人没让你说话。”说罢又返回谭安德身边,低头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