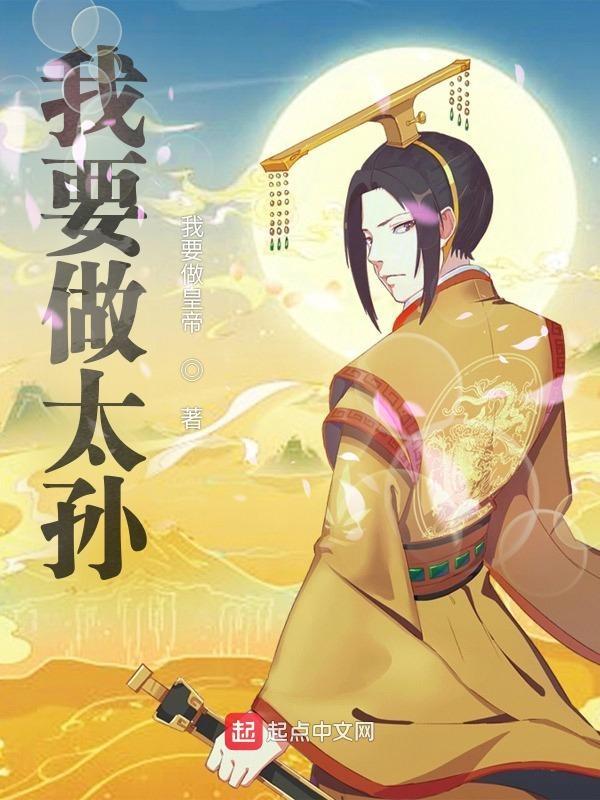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沉舟侧畔(第一部)红尘有梦 > 第10章 何为丈夫(第1页)
第10章 何为丈夫(第1页)
夜色渐浓。
一辆华贵马车驶入岳府,岳元祐轻身下马,步履轻快朝后院走去。
他如今深得知州大人器重,与提学大人交好,又有妻子挥洒钱财四处打点,眼下三年期满,不日便要擢升,想及家中年轻小妾,自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心情竟是好极。
未至内院,却见府中下人往来忙碌,拿轻搬重忙得不亦乐乎,岳元祐眉头一皱,吩咐身边长随小厮说道:“去问问岳诚,这是怎么回事!”
小厮一溜小跑去找岳诚,不一会儿便与岳诚一道前来,那岳诚上前一步恭谨回道:“老爷回来了?府里下人正在搬家,老爷请到夫人房里用饭,二夫人这里马上便能收拾妥当。”
“搬什么家?”岳元祐一头雾水却又不好发作,边走边道:“又关二夫人何事?”
“夫人有命,将大姑奶奶一家请到新宅,三姑奶奶房里东西也都另存了一处院子,还有树廷少爷也要搬过去,”岳诚手上拎着一柄蒲扇扇个不停,“午饭过后开始收拾,老奴想着先可着二夫人房里先搬,一来东西少些,二来搬过去了独门独院也方便些……”
岳元祐一听便即明白,只是这事妻子事先竟不与自己商量,有心发作却又不敢,尤其给二房小妾单独一所院子,与他而言实在天大喜事,心中喜怒交集,竟是一时无语。
“老爷?”
“没事了,你去忙吧!吩咐下人们也别弄得太晚,莫吵了夫人休息。”
岳元祐大手一挥,当先一步进了后院,几步进了正房厅中,却见门窗开着灯烛亮起,婢女采蘩站在珠帘边上,冲自己行礼问安。
“夫人呢?”岳元祐看厅中圆桌上摆着酒菜,站在当地由着采蘩脱去身上衣衫,只穿一件绸裤,披了件灰色道袍坐下吃饭。
“夫人今日身子不适,吃过晚饭便躺下了,老爷稍坐,奴进去叫夫人起来。”采蘩为岳元祐斟满酒杯,便要去里间卧房唤醒柳芙蓉。
“那却不必了,我用过晚饭就走。”岳元祐随手一挥,刚要在桌边坐下,忽然耳边响起一声细微低吟,他眉头一皱,回头问采蘩说道:“你可听见什么声音?”
采蘩双眼迷茫摇头说道:“奴婢不曾听见什么声音,莫不是老爷听错了?”
岳元祐神情一动,转身朝卧房走去,笑着说道:“晨起便没见到夫人,她总说身体不适,可曾请了郎中?”
采蘩神情自若,丝毫没有慌张模样,只是笑道:“夫人只是困倦,倒是不曾延请郎中,老爷您且慢些,等奴婢掌灯进来给您照着!”
岳元祐看她从容不迫,竟不拦着自己,而是回去厅中取了灯烛,心中暗怪自己胡思乱想言行莽撞,若是错怪了妻子,到时惹得她不快,再葬送了眼前大好局面,岂不得不偿失?
心念至此,他驻足而立,等采蘩进去点了灯烛这才进去。
只见卧房之内纱帐高悬,床中隐隐约约正躺着妻子柳芙蓉,许是听见这边响动,只听妻子问道:“采蘩何故喧哗?”
采蘩点好灯烛,笑着答道:“老爷回来用过饭了,心中惦记夫人要来看看,奴婢怕老爷摸黑进来摔倒,这才取了蜡烛过来点着。”
岳元祐笑着说道:“晨起便未见到芙蓉儿,日间当值时总是惦念,若非提学大人重托抽身不得,便早就请假回来陪伴夫人了……”
帐中柳芙蓉轻啐一口笑着嗔道:“这般年纪,不知跟谁学的油嘴滑舌!”
岳元祐走到窗前探手拂开床上纱帐,关心问道:“却不知夫人身子如何,若是难受,倒要早些请郎中诊治才是!”
帐中只有妻子侧身躺着,只见她秀发散落枕间,一身月白中衣遮住玲珑身段,面上微渗香汗,正定定看着自己。
岳元祐知道自己疑心太重,对上妻子目光心中便有些发虚,强作镇定神情说道:“瞧着芙蓉儿气色倒是不错,若是实在炎热,不如掀开纱帐通风纳凉!”
柳芙蓉轻翻美目,白了一眼丈夫说道:“妾身最怕蚊虫哼哼,你又不是不知!只是有些着了暑气,你赶紧吃饱喝足了去找晴芙,莫在我这里扰人清梦!”
岳元祐有些尴尬,讪讪笑道:“我也是一番好心好意,你不领情也就罢了,如何还要赶我!”
柳芙蓉轻哼一声不语,竟是翻了个身不去看他。
岳元祐放下心来,忽见妻子烛光昏暗之下粉面香腮满脸春色,眉目如画竟似比从前还要好看,心中跃跃欲试,虎着胆子说道:“不如我今夜便……便睡在这里……你我也好久未曾到一起了……不如……不如……”
柳芙蓉猛然回过头来,笑吟吟说道:“那你可想好了,若是这几日都未曾与晴芙欢好,倒还能堪一用,若再像那夜一般,弄得妾身不上不下,我可不肯轻易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