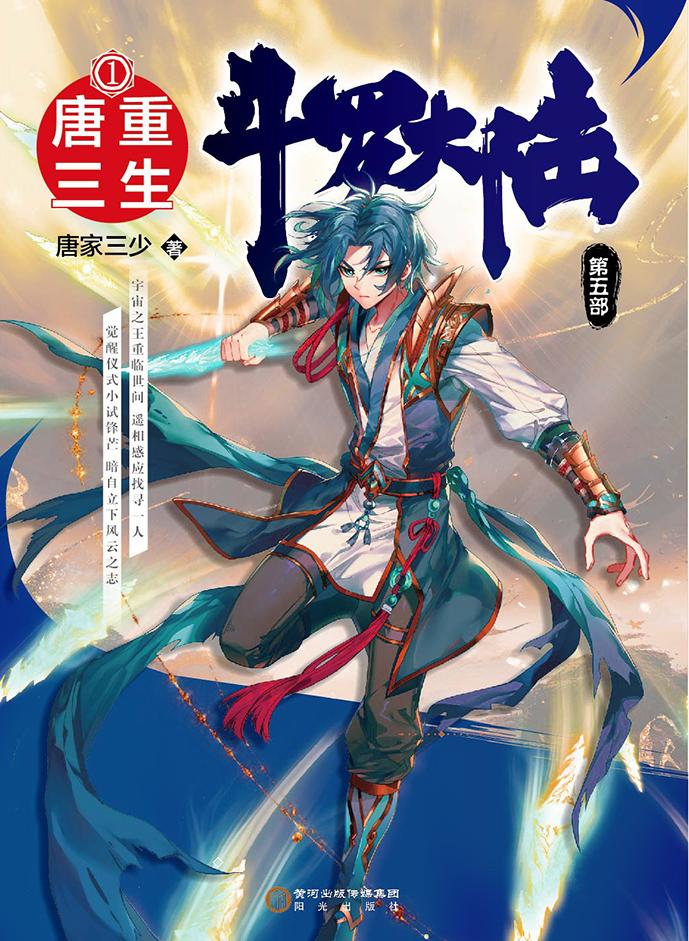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港夏烈吻 > 319 第317章 你怕什么(第2页)
319 第317章 你怕什么(第2页)
应铎的声音听起来依旧风度翩翩,像在所有媒体面前表现的那样:“等文教授返港,再携观棋登门拜访。”
“当然,再见。”文唯序没有多一句废话去关心唐观棋的现状,只落下这一句,便挂掉电话,好像真的只是普通师生。
但这举止却是对唐观棋的莫大帮助,她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应铎终于放开她,她大口大口喘息着,手撑在桌上都撑不住,一下瘫坐在椅子上。
她连多余的表现自己情绪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好像耳边眼前都是乱影,血管好像都麻痹,眼前闪起低血糖时才会出现的灰黑交替。
过了很久她才回神,视线落到自己手上的红痕,余光瞥见一只有个青紫到溢血牙印的手掌。
她才回神,抬起头看向手的主人,应铎正面无表情看着她,背对着光,眼神漠然。
她才意识到他一直站在那里看着她,背后莫名一寒。
以往总是温柔含情的面庞,线条凛冽到只看着他都觉得生畏,让人意识到他本来就是这种长相,而不是初见时她觉得的随和宽容。
像一个完全和她没有关系的审判官在平静审视她,高高在上旁观着她所有的失态,以此定她罪行深浅。
唐观棋用袖子随手擦了一下眼泪,只当好像没有什么事情生一样,重新拿起筷子。
哪怕她拿筷子的手无力到抖,根本没办法做出拿握的动作,她也做出无事生的样子。
应铎只静静看着她强演太平,演这连谁都骗不过的和睦场面。
唐观棋终于艰难用筷子夹起几粒米粒,听见头顶传来凉薄扎心的质问:
“高兴了?”
他将她在瑞典最喜欢吃的那道菜移到她面前:
“听见文唯序的声音,现在应该能吃得下饭了。”
瓷碟底部扣在桌上闷噔的声响落下。
唐观棋忽然把手里筷子狠狠砸了出去,但她力气太弱,筷子只是被丢出去几步之距。
她的声音很轻:“你说够了没有?”
应铎的脸上却一丝波澜和紧张都没有,仿佛根本不紧张她的想法,薄唇轻碰只说出:
“被我说中,很害怕?”
唐观棋感觉自己的呼吸道好像被冰结满,肺腑里都是结晶,再用力也吸不进一丝空气,无法相信每一句话都是从应铎口中说出来的。
应铎的声音冷漠平淡:“你刚刚到底在怕什么?”
唐观棋抬头看着他,没有说话。
应铎垂眸看着她,像看一个陌生人:“你怕文唯序听见什么?”
周遭安静得可怕,只剩下室内水景的嘀嗒声。
别墅里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从里到外都死一般寂静。
他的语气冷淡,像一个看她感情被肆意摆弄的看客,颜色薄淡的唇轻碰:
“怕他生气,还是怕他觉得我们很恩爱?”
唐观棋的声音很轻:“你别说了。”
应铎的眼眸压下来,睫线凌厉:“提到他让你很难受?”
唐观棋忽然拔高声音:“我让你别说。”
她起身就要走,应铎一把钳制住她手臂:“去哪?”
唐观棋咬着牙:“我不想和你待在一起。”
但她的每个字都在不自觉地颤抖。
应铎却没有放过她:“你是不是早就和他说过,让他在瑞典等你?”
唐观棋眼睛通红看着他:“我没有。”
应铎居高临下看着她,眼底是完全漠然的俯视:“那他怎么会知道在瑞典可以等到你?”
“我不知道!”唐观棋挣扎着要走,应铎大手握得她一步走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