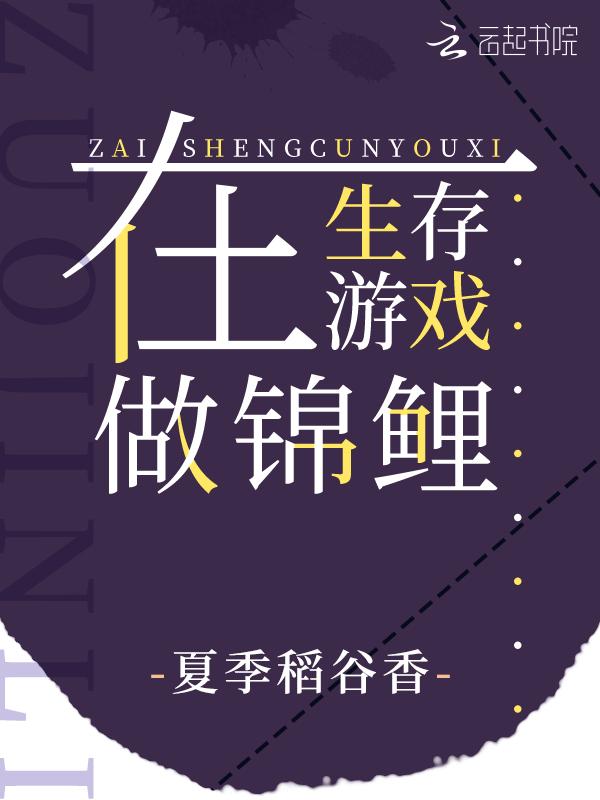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她不是潘金莲 > 番外合集(第5页)
番外合集(第5页)
他贴在她脖子上痴痴地笑了一会,又撑起来亲。她,带着点顽劣的得意,“怕不怕?”
西屏回过神来,一巴掌掴在他脸上。他不痛不痒,也不生气,盯着她满脸的泪水假装吃惊,“哎呀,你哭了?外甥真是不孝,怎么好这么对你?”
她的睫毛打湿了三两根的黏在一起,鼻尖也红着,在斜撇下来的阳光里,有一种神性,这神性却是脆弱的,轻而易举给他侵。犯了。他一面有些负罪感,一面又得意,手在她脸上温柔地搽着泪,眼睛迷恋地在她脸上打转,“可我就想这么对待你。”
西屏不由得翻了个白眼,这人不知怎么的,就喜欢说些没头没脑的呆话,就那么一点坏,全露给她了,难道这就是“杀熟”?
听见红药在甲板上喊,她忙推开他,胡乱抹干了脸,仰着头答应,“我在这里!”
时修先扶她上去,旋即自己也爬上来,欹在船尾的阑干上看西屏有点慌张地随红药从侧面的窄梯子往楼上舱房去了。他自转过身,想起方才她迷乱中说央求他“不要弄。到里面”,回味无穷地对着江水发笑。
有了这一回,她再看见南台也不是那么不顺眼了,何况还有臧志和从中调和着,硬是与其在船上和和气气地相处了一日。
次日下晌到了江都,码头上早有家下人等候,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只西屏一看见他便暗暗剜他,恨不得用睫毛在他身上掏几个窟窿出来。
西屏还住在先前那间屋子,嫣儿她没带来,从姜家走的时候放了她自由,顾儿便把红药和一个半大的小丫头给了她。南台仍住在时修院中的东厢房,他一定要给房租,顾儿推辞不肯收,次日午间他便拿来给西屏。
西屏为使他住得心安,只得代为收下,将银子随手一放,咦了声,“今日狸奴到衙门去述职,三叔新调来,怎么没去挂名?”
“我一早就去了,没什么事就先回来了。”南台在屋里转了转,见她那几口箱笼摆在墙根底下,里头还有许多衣裳没收拾完。她爱干净,衣裳换得勤,就做得多,也很爱惜,穿过几年的也像新的一样,她把它们都搬来了,他看着她这些行李,悲从中来,“二嫂真要在这里安家了。”
话里似乎有一丝酸楚,西屏明白他的心,微笑着请他榻上坐,安慰道:“三叔也该成个家了,如今可再不能等姜辛和卢氏为你打算了,你又没有别的长辈,该自己打算打算。”
这事情南台从未有过打算,从前是因为婚姻大事自由长辈做主,如今要轮到自己来主张了,却是想要的得不到,可得的又不想要。他几乎这一刻就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心里微微刺痛了一下,低下脸一笑,“我没什么打算,过一日算一日吧。”
西屏简直弄不明白他到底喜欢她什么,有些哭笑不得,也有些抱歉的情绪,觉得是自己将他耽搁了。她吁出口气,忽地欠身在炕桌上,俏皮地朝他眨了眨眼,“要不,我替你打算打算?你总不会信不过我的眼光。”
南台看着她逐渐鲜活的面孔,感到一种满足,笑着转过谈锋,“不说这个了。我是特地来问问二嫂,刚落脚下来,有什么要置办的没有?若有你告诉我,我每日下值路上好替你买办。”
“暂且想不到,”西屏不忍拂他好意,只得温柔摇头,“等我一时想起了再告诉你。”
不想听见时修的声音从门外头传进来,“三爷真是体贴,这些琐碎的事都想到了。不过我看就犯不着你操心了,六姨住在我家,我娘自然都替她打算好了,纵然一时缺个什么,还有下人去置办。”但见他微微冷笑着进来,望着南台又用不高不低的声音假装嘀咕,“我说怎么跑得这么快,敢情是趁我一时回不来,好捡空子钻。”
他是故意要给人听见,正好也一字不落都钻进二人耳朵里,南台却装听不见,不理他,也不让他,仍在榻上与西屏对坐吃茶。
西屏则嫌他说话太刺人,朝他乜一眼,“什么事在你眼里都像是有鬼。”
可巧红药抱着堆要洗的衣裳出来,忍不住也笑道:“二爷简直太多心了,这些心眼子都留着办案的时候用多好,没得用错地方。”
时修猝然觉得尴尬,坐在案前,翘着腿,横眉冷睇着西屏,一时无话。
吃过半盅茶,他故意要做给南台看,在这屋里随意得很,一会自拿点心吃,一会又踅进卧房里收拾好没有,站在门下朝里指挥着丫头归置西屏的东西,显得他不单是这家里的主人,连西屏的主他也做得。
南台坐了一会没趣,反正来日方长,他时时刻刻都能见到西屏,不急在这一会,便告辞回房去了。
时修竖着耳朵听他走出去后才回转身来,走到榻跟前睨着西屏,“你为什么和他说话总是这口气?”
里头红药一听见他质问,便忙招呼着小丫头出去了。他益发肆无忌惮,将凳子一把拽到西屏跟前,面对面做下去,姿态端得像在公堂上审问犯人。
西屏把脸低下去吃茶,“什么口气?”
“轻声细语的,温柔得很!”
“你几时见我粗声粗气地和人说话来着?”
他一时语塞,隔了会只得忿忿道:“我听不惯!”
西屏斜眼瞅着他生气的脸,好笑起来,“那你把我毒哑算了,我自小说话都是这语气,改不了。”
“咦,不见得呢,你小时候可不这样对我讲话。”
谁叫他年幼时候不是弄得自己一身脏,就是捉弄她,她此刻想起来还有气生,“谁叫你讨人嫌!”
那时候他讨嫌,还不是因为她总是一副高高在上不睬人的态度,急得人团团转,这才变着法惹逗。不过她肯睬他的时候,他倒恨不得将天上的星星也摘来送她。他想起她小时候,只觉又恨又爱,想将她揉作一团又轻轻展开,这情绪没出口,便掐过她的下巴来亲。
正要闭上眼睛,却给西屏推开了,横他一眼,“现今你可不好再这样,这屋里还多了个小丫头呢。”
他瞪着眼脸怄得发白,赌了气,那小丫头叫翠柏,十三岁,是她娘房里一个媳妇的女儿,这年纪最是藏不住话,不像红药,看见什么都要去说!
他无奈叹了口气,因问:“你和我娘说了么?”
西屏冷眼斜他一下,“说什么?”
“我们的事。”
原来顾儿还没和他说开,她有心使坏,故意不瞒地噘起嘴,“你不敢说,却推我去?难道我不要脸么?我要是说了,大姐姐一个不高兴,赶我出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