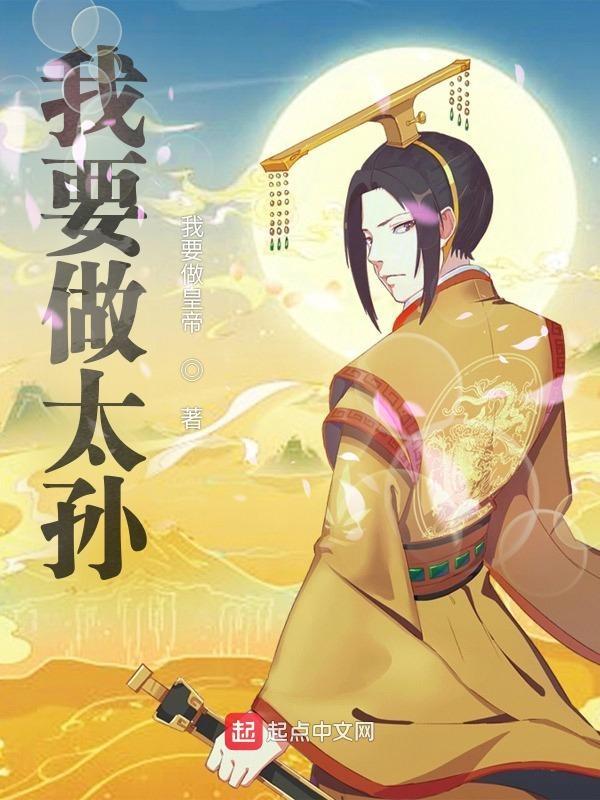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陷落春日 > 2030(第4页)
2030(第4页)
岑稚许站在原地,轻咬着唇角,纤薄的身形像冬日里的雾凇,脆弱到一折就断。
她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夜里要是遇了害,后果不堪设想。哪怕这地方不算偏僻,总有路人和车辆经过,但对方手里有刀,随便划伤哪里,都容易留下疤痕,以及心理上不可磨灭的创伤。
一股后怕从心底浮出来,谢辞序冷然的目光落向她,故作冷漠,“你等我,就不能挑个咖啡厅或者购物商场?”
虽然知道这是在关心她的安危,但岑稚许听不得受害者有罪论的话。语气淡淡地回:“我在哪等你都是一样,哪怕在酒吧等,也没有值得诟病的地方。”
这不算反骨,岑稚许并不觉得自己深夜外出有什么问题。
她瞥向几分钟前还处在癫狂状态的男人,眼里没有半分温度,“重点是在于,阴沟里的老鼠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臭婊子!我他妈知道你是谁!岑稚许,你别以为有人撑腰我不敢动你,光脚不怕穿鞋的,我就算砸了后半辈子,也要拉你下地狱。”
他语速极快,念及她的名字时,岑稚许面色微变,好在只是多一个轻音节,听不出太大区别。
这男人实在经不起炸,亏他曾经还是二代圈子混得开的人物,连这点定力都没有。
岑稚许哪里会怕这种小喽啰,不过碍于谢辞序在场,她还是得装一下心有余悸,下意识抓住了谢辞序的手。先前淋了点雨,掌心是湿潮的,被谢辞序宽厚的大掌罩住,暖意很快沿着四肢百骸钻进血液深处。
谢辞序用力地扣住她,指腹轻点,极有节奏地安抚着。粗粝的纹路仿佛透过手背,如同丝线般探进来,倘若她此刻真有他以为的那些情绪,也被这份缱绻驱散了大半。
可惜情绪作了假,她明明游刃有余,却要假扮胆战心惊。
“闭嘴。”
谢辞序只吐出两个字,薄凉的音色如同寒冰砸下,腿部发力,威慑力可见一斑。
当然,岑稚许并不清楚,究竟是气势上更强,还是谢辞序更擅长用敌人的疼痛来减少浪费不必要的口舌。
男人的喉咙被鞋底扼住,连个单音节也发不出来。
谢辞序打了个电话,言简意赅地提到了地点,剩下的话没什么可解读的。岑稚许隐约察觉,他的动作不会这么简单,回去后,肯定会把这个人的身份来历查个底朝天。
“待会警队会过来处理。”
解决安排完后续后,谢辞序撩起眼皮,上上下下将她打量了个遍。明明只是在检查她身上有无伤口,岑稚许却觉得这目光犹如实质,带着热与灼,勾起她本就算不得正经的旖旎心思。
他做事似乎很注重逻辑与顺序,确认她没有外伤,也没有磕碰的痕迹后,才缓着嗓问:“是你得罪了人,还是他犯了事?”
岑稚许眼瞳转动,思索几秒,试图揣摩他这么问的含义。
她那斟酌再三的样子,落到谢辞序眼里,自然成了不知该如何开口。料想到她可能也是过错方,还是个在校学生,要真牵扯到警察,心里肯定惧怕。谢辞序抬起手,用指腹摸了摸她冻得苍白发冷的面颊,“别怕,如果你是过错方,事情也不会追责到你这里来。”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那就好办了。
岑稚许低眸,静静听他说完,颈线仰起,同他对视。
她本就生得漂亮,皮相和骨相都没有缺陷,从这个角度望过来,像初获双腿后刚从深海潜上来的人鱼,染着不谙世事的白。明亮的眼瞳如同坠了星子,澄澈干净到没有杂质,让人无端想将她染上自己的气息。
谢辞序收回侵略的姿态,克制地心底燃起要吻她的欲念,声线放得更低,“现在好点了吗?”
岑稚许摇了摇头,“他这人就是咎由自取,我还嫌报应不够。”
“他是我朋友的校友,家里有点门路和关系,爸妈职位都不低,靠着收贿敛了不少财。明里暗里都不干净,高二的时候就骗了不少女孩的初夜,得手以后就借用权势逼人家取卵、代孕,他做中间商,吃了高额差价,那些女孩退学的退学,个别不甘心想要报复的,又被校园霸凌。”
岑稚许谈及这些事,只觉得胃里一阵一阵泛着恶心。即便已经过了这么久,那些女孩也已经被妥善安置好,后来岑女士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以帮助不慎误入陷阱的女孩调理身体,她还是本能地感到愤怒。
谢辞序听完,眼神逐渐深冷,握住她的骨掌绷紧。
“后来?”
“我把他爸妈贪污的证据投到了纪检委那,又雇了几个营销号和职业撰稿人,曝光了这些事。他爸妈被判了无期徒刑,他也被退了学,没多久就销声匿迹了。”
事情当年在网上小爆过一阵,岑稚许将其中的细节删减了部分,再讲述给谢辞序听。这人是京市的地头蛇之一,家族关系盘根错杂,寻常人要是敢举报,肯定被吞得连骨头都不剩。她那时到底还是个高中生,处理不好背后的关系网,最后还是谈衍出面解决的,岑琼兰也为此费了不少心神,家里那年的生意也屡屡受挫。
不过岑琼兰并没有责难她,只告诉她,在为别人出头之前,需要先想好退路,有十足的把握,才能一击毙命、斩草除根。
岑稚许那时候心软,想着他还是未成年,应该留有一丝悔改的机会。
现在看来,人性的坏已经刻在了骨子里。
怜悯不过是多余的徒劳。
谢辞序没想到故事的源头竟然是这样,看向岑稚许的目光多了几分深沉。她不似表面那样脆弱,需要让人时刻怜爱保护,骨子里藏着柔软与坚韧,会共情受害的女孩,也能在众人皆畏惧强权之际,勇敢地站出来,薄冰亦有盔甲般坚硬。
“阿稚。”他低声,“你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