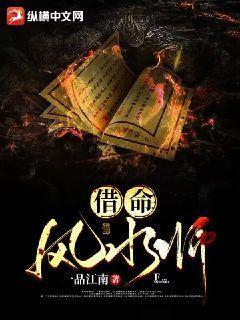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我,恶女,只想造反 > 8090(第6页)
8090(第6页)
裴长秀亦是诧异,两州因着有长平郡做缓冲一直都相安无事,不明白好端端的怎么就在该郡打起来了。
一行人快马加鞭匆匆回京,州府里的陈恩紧急调兵援助,因着朱州实力不可小觑,几乎所有武将都出动了,纷纷赶往战场。
朱州那边怒不可遏,州牧任在康义愤填膺,痛骂惠州欺人太甚,因为打死的官兵里有一位都伯是任家的表亲。
长平郡太守和稀泥的态度惹恼了任氏一族,当即发兵讨要公道。结果那太守为自保连夜求助惠州,惠州这边自然容忍不了朱州兵占领长平。
你发兵,我也发兵。
原本只是简单的互殴,不曾想演变成上千人的群殴。
眼见两州不打也得打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交州至关重要,因为要防备许州生事。
陈贤树接到朱州战事的消息,也很诧异,他虽然对京中的父亲有埋怨,但一码归一码。若两州交战,许州出来掺和,那大家都别混了。
陈贤树当即命官兵们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日夜巡逻,严防许州。
与朱州一战关乎存亡,裴长秀奔赴战场,临走那天陈皎相送,说道:“珍娘定要平平安安地回来,我还等着你北上。”
裴长秀骑在战马上,居高临下道:“一个都不能少。”
陈皎:“一个都不能少。”
说这话时,她的心中其实有些忐忑,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目送那群将士们离去,陈皎站在城门口,久久不愿离开。马春道:“主子回去罢,你连日奔波,也该好生歇两日了。”
陈皎忧心忡忡,“朱州养精蓄锐多年,它不比朝廷,这场仗极难打。”
马春:“我们也不差,手里有那么多厉害的武将,个个都是顶好的,他们定能凯旋而归。”
陈皎沉默不语。
崔珏冷不防道:“九娘子且回罢,战场之事就交给徐兵曹他们,那是他们的专长。你我能做的是不要拖他们的后腿,把粮草之事供给充足才是首要。”
陈皎看向他,“崔郎君所言甚是,州府里不能拖他们的后腿,若不然谁也活不成。”
崔珏残酷道:“倘若他们连朱州都拿不下,日后就别妄想着跟北方的胡人打了。那边的敌人比南方的汉人凶残千百倍,他们可不像这边的朝廷和交州那般经不住事。”
陈皎道:“朱州强盛,连朝廷都不愿意去招惹,这一战来得实在太快。”
崔珏宽慰她道:“我们也不差,那边再强盛,但数年没有经历过战事,难免懈怠。而我军这两年皆在征战,上了战场自要比他们敏锐许多。”
马春也道:“对对对,崔郎君说得极是,俗话说刀不磨不锋利,咱们惠州兵一直都在磨刀石上呢。那朱州已经有好些年没打过仗了,反应肯定没有我们的兵迅速。”
两人一唱一和,陈皎才觉得心里头舒坦些。往日攻打交州和奉州,她一点犹豫都没有。但朱州不一样,它是一头猛虎,甚至能吞并惠州。
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陈皎没法上战场,只能祈祷裴长秀他们能平安回来。
与朱州的冲突搞得京中人心惶惶,惠州那边亦是如此。
紧邻长平郡的江都已经进入备战状态,一些百姓出逃,一些则死守家园。
这两年州府把地方官绅清查后,衙门风气得到改善,当地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往要舒坦得多。
衙门里的张县令主动疏散百姓出城避难,但人们都不愿意,说要与惠州共存亡。
张县令不免窝心,高声道:“诸位且听我说,战事一旦打过来,咱们江都恐不保,还请诸位先行撤离,保住性命要紧!”
人群中有人问:“张县令,惠州兵保不保咱们?”
张县令道:“惠州的兵,是你们供养的,咱们九娘子曾说过,惠州兵不是欺辱百姓的强盗,而是护百姓的城墙!
“诸位供养着他们的粮饷,他们也是诸位的子弟,自要与老百姓共同进退!”
一老媪道:“我儿是惠州兵,只要他不退,我这个老娘就不会退!”
“说得好!只要咱们的惠州兵不退,我们就不退!”
“对!只要朱州人敢打过来,我们跟惠州兵一起打过去!”
“打过去!谁敢来进犯,统统打回去!”
一时间,聚集在街道上的百姓纷纷对朱州喊打喊杀。他们不愿逃离故土,而是选择跟惠州的官兵站到一起抵御外敌。
那种军民一体的凝聚力令张县令动容不已,似乎在这一刻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民心。
数年前陈皎拼命散播下的种子在这一刻萌芽,官民共治,军民一体,得到了具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