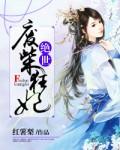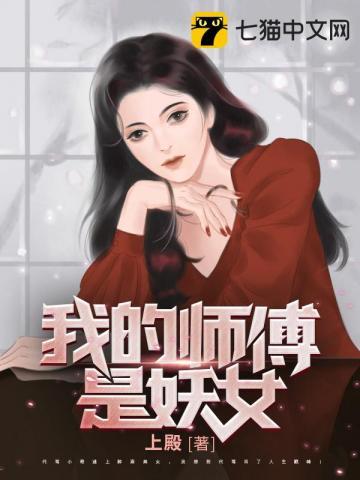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法医大佬穿成太医 > 15第 15 章(第2页)
15第 15 章(第2页)
这话与其说是自谦,倒不如说从一开始就对他的说法不甚赞同。
谢行眼神一顿:“还请先生指教。”
徐鹤来却不开口,转身重新入座,提起那支未干的毛笔。
谢行上道地跟过去,默默杵在背后,盯着他平直的肩膀。
这回徐鹤来写得很慢,笔画四方端正,所以就连谢行也能轻而易举看懂。
展开的白纸上,新添了八个字。
——不求济世,但求济人。
“某为医之初,恩师江公曾以此话相赠。你既然无心求学,我教无可教,也只有这句话可以相送。”
说罢,徐鹤来收起意味深长的目光,这才给出谢行最开始想讨的回答。
“至于何去何从,你自己斟酌便是,太医署绝不强人所难。”
……何去何从么。
回去的路上,徐鹤来的话仍不时回响在谢行耳边。
他对那套咬文嚼字的大师箴言没什么兴趣,更懒得去琢磨其中深意,唯独疑心最后那句——应该不是威胁的意思吧?
总归太医署不是传说中的东厂西厂,至少不会在物理层面上出手。
正悄悄在心底琢磨着,身下的马车陡然一停,将他乱飞的思绪震了回来。
“客官,到了!”车夫高声提醒。
谢行赶紧交钱下了马车,往前走了两步,停在一间客来客往的铺子面前。
日正中午,阳光将挂在铺面上的牌匾照得熠熠生辉,正是他之前来过的吴氏药市。
谢行才刚进门,马上就伙计头子眼尖地瞧见。
“哟,生员老爷来啦。”对方笑吟吟迎过来,刻意拔高了音量,以显示自己消息灵通,“恭喜恭喜,那句古话怎么说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这句老爷却喊得谢行鸡皮疙瘩直冒。
他专程过来,当然不是为了上演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烂俗把戏,只不过是因为还欠着吴老板一吊钱,得先把债务清零。
“这可真是巧了。”听他说完来意,药市的顾账房不由失笑,“刚巧吴公也有个远房侄儿高中,这会他已经去那家道贺了。你要实在着急,我先立收账的字据如何?”
谢行倒不在意这个:“不用那么麻烦,您收了账,替我转告一声就是。”
这笔欠账,原本就没有打借据,自然也就不必要收据。
他之所以先来这里,一方面是为了还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早点将整块官银兑成散碎铜板。
要知道,在冶炼技术有限的古代,银的购买力远高于铜,揣着银子的风险也更高一些,换成铜板,至少不用那么担心被贼惦记。
顾账房却不知道这些想法,只见他心眼诚实,且无半点小人得势之态,倒暗暗有些佩服吴得隆看人的眼光。
他也就不再多话:“行,您跟我来。”
顺利清完旧账,等谢行揣着重重几贯铜板回到谢家的时候,已经是晌午过后。热闹了一整个早上,报喜的信人总算是走了,只剩谢夫人自个儿满心欢喜地扫着一地纸皮。
“娘。”谢行径直走过去,将还热乎的一包铜钱递过去,“这是我刚从官府支来的盘缠,还是先交给你保管吧。”
谢夫人脸上笑容一怔,没想到儿子一大早出门就是为了这个。
她心头有些酸,也有些热。
“你啊,每次不管得了大钱小钱,都说给我保管,知道的说你孝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个吃铜子儿的母老虎呢。”谢夫人擦了擦手,却没有接钱,反而往回推了推。
“都要及冠的人了,总得学着自己理账,以后成家立了业,别学你爹做甩掌柜,叫人家笑话。”
“……那叫超然物外!”隔旁门缝里立刻钻出谢官人反驳的一句。
“你清高,你还管我说话作甚?”谢夫人反唇相讥一句,接着转回脑袋,小声说道,“隔壁李嫂子才刚和娘说过,选上了生员,官府还给贴补进京的盘缠。你仔细收好,别叫旁人知道,这叫财不外露。”
官府对人才的补贴,充其量也就十几两银子,固然不能算小钱,但用财来形容,可见他们家的实际经济水平。
谢行也正打算和她商量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