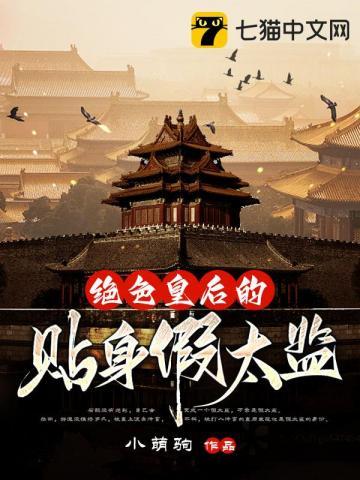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重生成卧底但秒掉马 > 鸲鹆沟(第1页)
鸲鹆沟(第1页)
“掌令遣我来问瞿姑娘,答应他的事何时才能做到?若瞿姑娘迟迟不履行约定,那姑娘想得到的消息也莫怪掌令不肯出力了。”因这话,原本面容清秀的少年面庞沾上阴鸷。
看着面前咄咄逼问的元冬,瞿芙心里漫上了无可言说的烦躁,也许她就当初就不该同于潮这种人交易,指尖掐进膝间裙,她咬牙道:“今夜子时,你们带几个人去鸲鹆沟。”
“那小子就去禀告了,瞿姑娘可别让掌令失望。”元冬正要告辞,窗外霍然传来石子落地之声。
“谁在外面?”二人警觉,赶忙冲出门外。
左右环顾,竟无一人。
在玉珍不小心踢到檐下石子时,明春即刻拉着她连连拐过几处窄巷才停下。
两人躲在巷道僻静处,确认瞿芙元冬没有追上来,各自靠着青墙喘气。
明春气刚理顺,就听玉珍说:“那个元冬是于潮的手下,我见过。”
她亦有印象,上次在商道院,于潮让她转交扁玉时提到的人就名为元冬。原本自己只是怀疑瞿芙,没想到今日竟直接抓着她与于潮勾结的现行。
瞿芙想置她于死地……明春的手指不自觉抚上藏在袖中的匕首,她本不想做到这个地步。
“我们应该告诉郑管事。”玉珍突然开口。
“不可!”明春急忙阻止。
“为何?”玉珍目光灼灼,“明春,你当我傻,上回问查院来得那般突然,随便一搜就搜到了什么云光的信,没有人暗中相助我是不信的。再有,格子箱的钥匙除了我们七人有,也就剩江掌令了,不是江掌令,不是你我,刚才又看到了那档子事,还能是谁?”
“那日你虽机敏暂且避祸一次,可下回呢?你和云光的字迹月银簿上都有留存,或许当时旁人不察,但难保以后不会旧事重提,此事必须告知郑管事。”她说完,转身就往郑观堤杂事房的方向行去。
上回事情暂搁,明春本以为就此打住,没想到在旁人眼里还有如此纰漏,难怪方才瞿芙在她写字时不发一语。
告知郑管事或可预防此事再次发生,但她定不会仅凭自己与玉珍的一面之词就处置瞿芙。
若她寻了瞿芙一同问话,瞿芙借机将她是齐王卧底的身份托出,即使缺少证据,即使瞿芙被处置,此事落定后以郑管事的疑心,她也难逃一查。
明春死死抓住玉珍的胳膊,冥思苦想半晌才勉强胡诌了一个借口:“我们没有证据,直接去告诉郑管事也是徒劳,方才瞿芙说了今夜子时鸲鹆沟,不如你我到时直接抓她们一个现行,再去禀报郑管事也不迟。”
玉珍想了想,勉强应下。
说通后,两人各自紧绕着对方的胳膊回了通院。
刚回程不久,玉珍又被叫去山上打扫昨夜昏礼残局,临走时还几次耳提面命要求两人今夜一同前去鸲鹆沟,明春连声答应,她才放心离开。
而明春因得了孙兼令的赏,省下半日功夫,在房间睡了一下午的囫囵觉。梦中光怪陆离,她惊醒了好几回,醒后没多久又因身心俱乏昏了过去。
这觉虽睡得不太安稳,但好歹也养回些精神头。
彻底清醒时,窗格上已显出幽蓝之光,明春强忍住喉间不适撑臂起身,正巧玉珍从门外的昏沉夜色中走来,在窗边点了盏灯。
不过是萤萤灯烛,明春却安心许多。
玉珍拭干脖间和额发上的汗,走近她,声音小得几近不可闻:“我还要上山一趟,回来时可能会晚些,子时的事千万莫忘了。”因着门外催促,只稍作停留便又走了。
明春起身穿衣,先将匕首藏于靴中,又寻了方巾帕沾上迷药塞进袖口,刚一一备好晚间要用的蜡烛活火折,瞿芙与其他人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戌时已尽,入亥定昏。
半个时辰后,大家一一擦完身躺下,明春忽从床上起身走到窗边坐下,看了眼窗外天色,厚云遮月,林中寂静,夜色似乎比平日里更暗些。
她提起刚才备好的竹篓,问众人:“这天实在闷热得很,有人要一同去纳凉么?”
杂役院除了冬日供应热水用以沐浴,其他时节浴房都落了锁,女孩们只得在房内擦身洗浴。
夏日溽热,活计又多,上山下山一趟浑身就裹满了汗。
她们不比那些整日沤臭逼人的须眉浊物能忍,不出三五日便要打水沐浴,但水井又离通院甚远,来回提几桶水就要花去小半个时辰,便有人偷摸着在鸲鹆沟附近造了间简陋浴房,女孩们时不时相邀同去,又怕郑管事知晓后责怪,只得说纳凉二字。
其实郑观堤又何尝不察,只是同感女子不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大家一听,皆摇头称今日太累了不去,瞿芙忽站起身道:“阿春,我陪你。”话罢两人各搀扶着,往山脚的鸲鹆沟行去。
今夜夜色昏沉,两个人走得很慢,大约一炷香后才走到鸲鹆沟前的小山坳上。
纵目眺望而去,几条小河在谷底穿插交汇流过,水畔草木郁郁,时有夏虫鸣叫。
明春将藏在身前的云光信件拿出放在竹篓中,对着瞿芙微微一笑:“险些忘记把它们带来了。”说完,两人沿着小路往谷底腾挪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