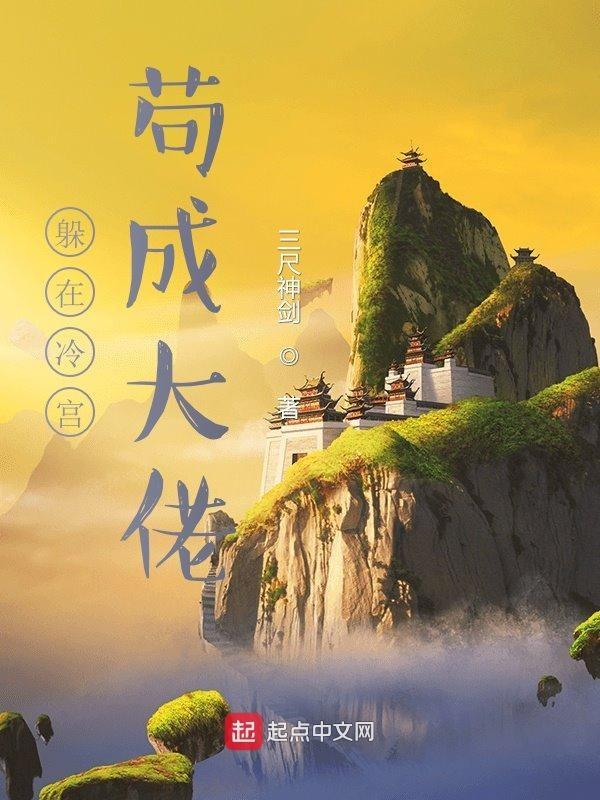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在怪物世界修仙 > 民国戏伶13(第1页)
民国戏伶13(第1页)
白月棠径直闯入督军书房,单刀直入:“我要救奚阳的法子。”
督军手中茶盏一顿,面露惊讶:“你怎会知晓……”
“督军何必惺惺作态?” 她唇角勾起讥诮的弧度:“督军府戒备森严,五步一岗,我竟是来去自如半分没有人阻拦,那日偏生让我听见,不正是等着我心软前来自投罗网吗?”
督军沉默良久,长叹一声:“需将你彻底转化为海灵,方可开启祭祀。符文……要刻进骨血,过程……会很痛苦。”
“当日在我戏服绣咒时,倒是不见督军心软。” 白月棠冷笑,“我只问一句,有几分成算?”
“祖籍记载……不足三成。”
“我应了。”白月棠打断道,“但需应我一事——不要让奚阳知晓。”
督军猛地抬头:“你——”
“若我死了,就说我赴洋留学。”她捏着袖口中奚阳给的糖果,“他那样干净的人,合该一世清朗,不该背着人命过活。”
“若失败……”
“那便是天定的缘分,要我们做对亡命鸳鸯。”她突然笑起来,眼角闪着泪光,“兴许下辈子能当对寻常夫妻。”话音骤冷,“但你记住,我的命是我自己的,轮不到旁人做主!”
督军退后半步,终是深深作揖:“你是好孩子,是老夫……对不住你。若是成了,你还活着,老夫亲自为你们主持婚礼。”
白月棠重新穿上了那件绣满符文的戏服,日常也并不换下。每当夜深人静,她便独自在戏台上唱念做打,音调哀怨婉转,水袖翻飞间,那些诡异的纹路在月光下隐隐泛着幽蓝的光。
白日里,她会换下戏服两个时辰,守在奚阳塌前。少年的气色日渐好转,她的面容却愈发苍白,连唇上的胭脂都遮盖不住那股灰败之气。
“月棠,你脸色不太好……”奚阳心疼地触了触她消瘦的脸颊。
“还不是怪你,”白玉堂佯装哀怨地横了他一眼,眼波却温柔:“白天要哄你喝药,夜里要练新戏,这般折腾,脸色能好看到哪里去?”指尖轻轻点在他的眉心,“你早些痊愈,我才能睡个安稳觉。”
奚阳笑着拱手作揖赔罪:“是是,我定快快好起来。”
她忽然握住他的手,十指相扣,深深地看进他的眼底:“奚阳,娶我可好?”
奚阳呼吸一滞,片刻后苦笑地扯了扯嘴角:“棠儿,你知我这身子……”
“我白月棠此生,非君不嫁。”她打断他,眼中闪着倔强的光,“还是说……少帅嫌我是个下九流的戏子?”
“胡闹!”奚阳急得咳嗽起来,“我待你如珠如宝……怎会轻贱你!”
“那我要做少帅夫人。”她凑近他耳边,温热的呼吸拂过他的耳尖,“风风光光的那种。”
良久,奚阳轻叹一声珍而重之地在她掌心落下一吻:“好,待我病愈,必以八抬大轿迎你过门。”
中秋月圆那日,整座城都浸在喜庆的大红里。督军府备下的红妆从正门一路铺到戏班门口,丝绸喜布在风中翻飞,含着无声的凄凉。
奚阳身着红锦缎马褂,骑着雪白骏马自督军府缓缓而来,平日里苍白的脸色被喜服映出了几分血色。所到之处,百姓纷纷撒出早已备好的花瓣。
戏班厢房内,白月棠静静端坐在梳妆台前,盖头垂落的流苏随着她的呼吸轻轻晃动。红绸映照下,她本就精致的妆容更添几分艳色,完全掩住了原本灰白的面容。
督军端坐在督军府正堂的太师椅上,侧位上的戏班班主只敢挨着半边身子坐下,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满脸惴惴不安,督军瞥他一眼,“端正坐着,阳儿的意思,不必有什么顾虑。”
班主压低声音,用仅二人可听见的音量道,“大人,今晚……就是月圆之夜了。”
督军轻叹了口气,“遂了孩子的心愿吧。你去准备祭坛,其他,等拜完堂再说吧。”
喜乐声由远及近,奚阳一手执着红绸,一手搀扶着遮着盖头的新妇步入正堂。
“一拜天地——”新人向着大开的雕花木门缓缓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