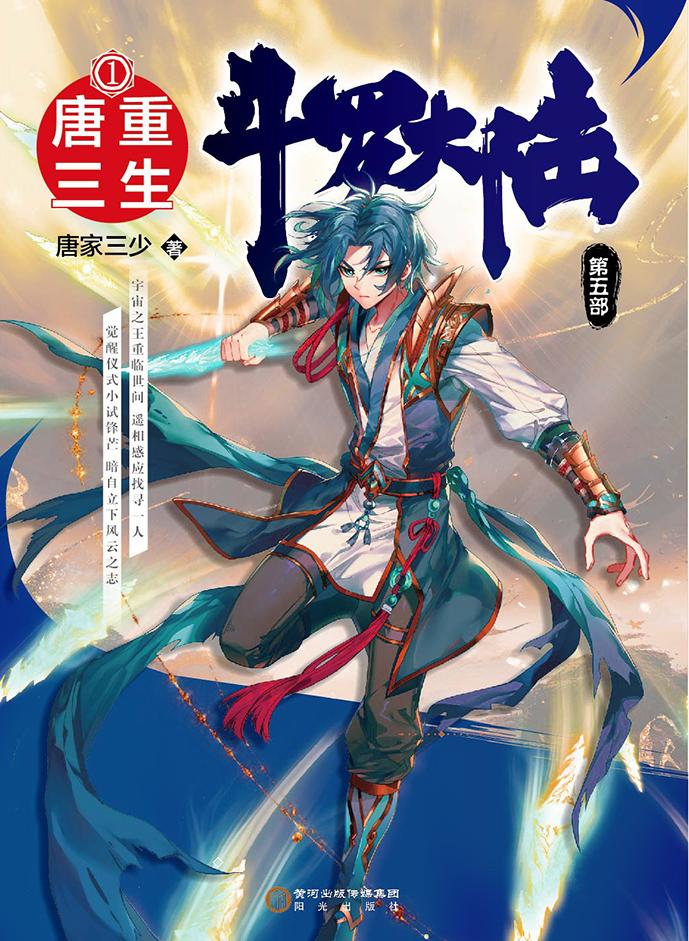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雪落青松 > 击鼓(第1页)
击鼓(第1页)
奉元帝亲政后,还是头次罢朝而归,并一反往日仁和形象,不顾群臣谏言,连下三道圣旨。
刑部侍郎林知珩,渎职徇私,撤职下狱,此为其一;
兵部尚书齐宗柏,自首供罪,收监待审,此为其二;
北疆异心起于京都,暗通款曲必有结党,本案水落石出前,关联人等监管以待,此为其三。
此番威压,令群臣骚动更甚,个个奋笔疾书慷慨激昂,送往御书房的奏本接连不断。
奉元帝始终不予回应,群臣蓄势待发等待朝会,不成想皇帝称病歇过,众人又扑了个空。
三月初三,距下次朝会前两天。
当朝中书令林仲检独女林知瑶,素衣脱簪出现在宫门登闻鼓前,为父击鼓鸣冤。
此事一出,奉元帝当即下令以煽动舆论,扰乱司法罪,命禁军前去将人拖走。
是时,禁军统领仍是梁安仁,君令不可违,遂带兵而去。
行至宫门。
击鼓之人已由林知瑶改为梁颂年,夫妻二人站于阶上,风骨峭峻,让人见之怯步。
梁安仁快步上前,遏止道:“住手!”
夫妻俩充耳不闻,梁颂年动作不停。
梁安仁怒道:“梁子渊!”
梁颂年仍是不予理会,林知瑶视线投了过来,神色淡淡道:“公公,您此刻正当职,还请在官言官,莫以私情动恻隐。”
梁安仁闻言气的不轻,抬手示意身后禁卫停在原地,自己则迈到台上。
“今日我若抓了你们,就是把陛下推到了风口浪尖,坐实了独断专行的态度,你们当真要把局面闹到这个地步?”
林知瑶面不改色道:“儿媳知道这案子天大,也愿配合调查,只是在无证无据的情况下,将我父亲关进诏狱数日,我们做儿女的,实在无法安坐家中。我没法像兄长们那般上书陈情,只能来敲这登闻鼓,恳求圣上一视同仁,放我父与其他臣工一般,于自家禁足。”
梁安仁听不下去,转而去抢了梁颂年的鼓槌,将气撒到了他身上,“别敲了!”
梁颂年手上猛的一空,愣了愣,然后非常不合时宜的道了句:“父亲要试试吗?”
梁安仁听了,抬手就给他了一槌,“什么时候了还打趣你老子!”
梁颂年往林知瑶身后站了站,不吱声了。
梁安仁见状,怒骂道:“混账,她关心则乱行差踏错,你不知道拦着,跟着胡闹什么!”
梁颂年理直气壮道:“夫妻本是一体,如今她日日难过,儿子心里也跟着煎熬,何况……”
他说着完全藏在了林知瑶身后,“她说的合情合理,陛下该允。”
“你——”
林知瑶开口打断道:“若我们真是无端生事,公公为何不直接抓了去?好言劝阻,无非是心中明镜,事态如此,还望如实禀明,请陛下裁断!”
她说完,伸手扯过梁安仁手中鼓槌,转身挥起胳膊,一下一下又敲了起来。
梁安仁闭了闭眼,好半响才叹了口气出来,然后转身离去。
不等梁安仁面见,奉元帝已经听人报完了全部过程,沉着脸半响不言,最终并未表态。
梁安仁路上想着会发生的各种情形,连负荆请罪的准备都做好了,怎么也没想到直接让奉元帝给拒之门外了。
他呆楞在殿外,好久才反应过来,然后带着满脸的不可置信退下了。
到傍晚的时候,林知瑶敲鼓鸣冤这事,已经传遍了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