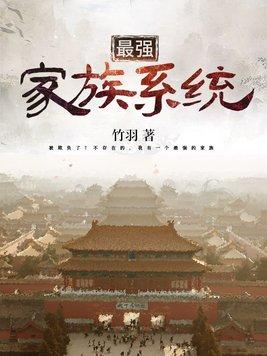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她下围棋主打暴力净杀 > 本相(第3页)
本相(第3页)
“如果再是这种棋,不要来浪费我的时间。”
语罢径自捡起桌边的保温水杯,拎起椅背上的手包,离开。
留下仇嘉铭一个人,缓慢地收拾棋桌。
他这时才想起来,还直播着,将最后一捧棋子归入棋碗之中,合上棋碗的盖子,取下支起拍摄的手机,对着镜头,又摆出他最娴熟的满不在乎的笑:
“哎呀观众们,看来我能力不够,学艺不精,新策略没派上用场。……没关系!那咋了!这不是三次机会还剩一次吗!江陵长玫实在不要我,我再投投别的俱乐部,老天还能绝了我的路不成……”
杨惠子讨厌他讨好观众时油滑的笑声。
这笑声像是在仇嘉铭面上层层叠叠涂抹着的劣质颜料,令她见不到他的本相,只见到一张浮夸虚伪的假面。
她看一眼表。八点多,正好下班。
走出江陵长玫训练室所处的商业楼,她察觉到自己的润唇膏落在训练室里了。
这也不是什么非要带回家的东西。
但给了她回去一趟的理由。
她一边摁亮上行的电梯,一边在心里默默发誓:如果她回到训练室,看到仇嘉铭还在捣鼓他那狗屁直播,还在笑嘻嘻地假装不在乎,她就不管什么润唇膏了,她立马掉头回家,从此见仇嘉铭一次,骂他一次。
训练室里漆黑一片。
杨惠子打开灯,偌大的棋室里空无一人,仇嘉铭不知道去哪了。原先她站着看棋的地方,没有她的润唇膏。她又顺着走廊,往卫生间里找。
半路上,灰白墙壁边,一个身形健硕高大的男人,蹲着团在墙根,大脑袋圈在手臂里,身体微微抽动。听到杨惠子的脚步,他似极力压抑了情绪,但仍不时泄出一两声啜泣。
仇嘉铭在哭。
趁所有人都下班了,找了个靠近厕所的位子,哭得像只找不到回家的路的大狗。
“搞什么……”杨惠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仇嘉铭从臂弯之间,探出哭湿了之后显得皱巴巴的眉眼,自暴自弃地:“怎么又是你?你嘲笑……”
杨惠子在他面前蹲下,伸出双臂,将他很小心地圈进自己怀里。
仇嘉铭体格太大,杨惠子只能环住一半,手掌落在他宽厚的脊背处,像哄孩子似的,很轻地拍着。
仇嘉铭像吓着了,身体僵硬,一动不动。她的怀抱温暖轻盈,像盘生在野地废弃的巨石之上,一株很小的菟丝子。她身上的气息淡雅柔和,是一股清晨微风里捎来的初开桂花香气,蔓延在他身侧,像是菟丝子探出的脆弱盘旋的藤蔓,牵扯着他。看似是菟丝子依附巨石而生,可事实分明是巨石仰赖这一刻的牵扯,而不至于分崩离析。
“哭吧。你的沮丧,伤心,不甘,把它们都哭出来。先正视你的情绪,才能战胜它们。”
她吐字诚恳清晰,却如咒语,仇嘉铭听不真切。
他记起三年前,他与杨惠子堪称朋友的一瞬。那一晚,他输了棋,在酒吧喝酒消遣。杨惠子坐到他身边,告诉他,自己是他的粉丝。杨惠子二十出头,生得甜美喜人,笑时颊边酒窝鲜明。一开始,他只想在年轻女粉丝面前吹牛。但杨惠子陪了他整夜,陪到酒吧关门,两人并肩散步,穿过半个岳州城,直到岳州江边浅滩,破晓时分。
他兴许是喝多了。此刻他对于杨惠子,除了名字,一概不知,他却把职业人生中的所有困顿时刻,全都倾吐给了身侧的女孩。
后来他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不相信眼睛圆溜溜、看起来善良真诚的姑娘。
他想,恐怕他又要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