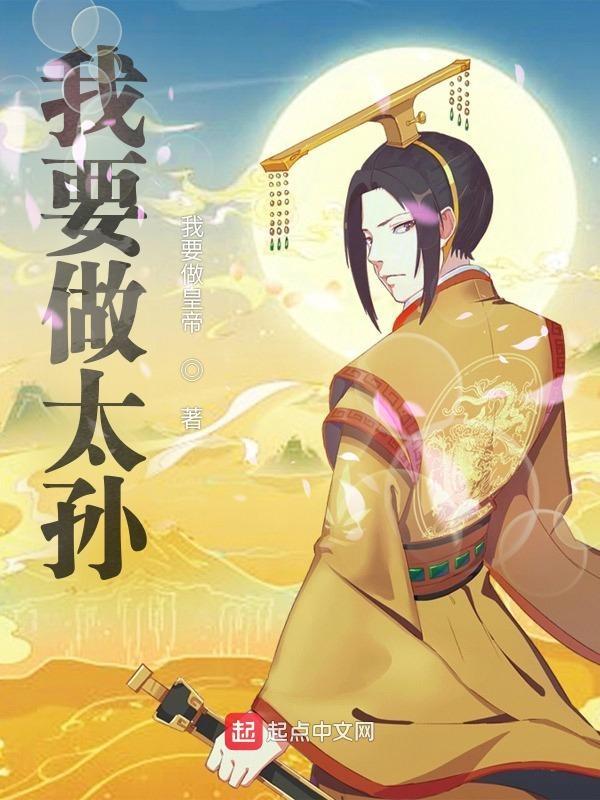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武侠异世界 > 第2章 夜话(第2页)
第2章 夜话(第2页)
随后王主事又说了很多道听途说的死士营故事,真真假假,有些纯粹是民间的意淫,什么死士营在战场上冲锋前先下马做爱,高潮后提升功力再上马冲锋。什么死士营后期为了千里追击胡人王庭,一人三马,打破了不纳妾的誓言。呸呸呸,据我所知,死士营各个都是好样的,他们跟随常将军一直打到北海边上,殄灭胡人黄金可汗嫡系,挖出所谓第一代的黄金天可汗脑袋做成酒器,使的胡人再也不能一统,至今都相互攻伐无休。天下太平后,太祖给了他们丰厚的奖赏,剩余的死士营均解甲归田,跟老婆安心回家生孩子去了。据说最终活下来的几百人没有一个纳妾的,战马决的秘密也被隐藏的很好。
试想,要是战马决泄露出去,肯定会有会有很多父母将女儿训练成母马,以图卖个好价钱。世人本就重男轻女,大量女孩无缘去义学读书,不识经脉不能成为高手,她们的一生只能奉献给家庭。女性武者不足武道人士的五分之一便是明证,太祖皇帝不让马犬鱼这些六畜决流传出去实在是太明智了。据说只有太祖的亲信大将,为了提升他们的战力,才得以传授六畜决,现在都是各家勋贵压箱底的宝藏。
此外,太祖爷定制,皇帝一后二妃,其余再受宠的也只能是类似女仆的高品级宫女,而且只有一后二妃才有资格生下皇子。传说这种定制,就是为了让皇后练天马决,皇贵妃练地犬决,皇妃练人鱼决。练习六畜决的女性需要常常保持赤裸拘束状态,心理也越来越深爱服从双修的主人,往往主人死后郁郁寡欢,不出十年便因过于思念主人,郁郁而终,因此大武朝从来没有过后宫干政现象。虽然太祖爷这招对后妃们太不友好,但是对国家稳定确实是非常有利的,小节有亏而大义无损。
但不知道,有些国家大典,皇后盛装出席的时候,官老爷们会不会因为联想到皇帝骑胭脂马的场景而笑出声来?
史书记载,太祖爷带兵打北胡的时候。多带马皇后,胡皇贵妃出征。而去打陈瞬恨的时候,往往带马皇后和万贵妃出征。似乎就跟她们的修炼功法相性有关。后续皇帝也有类似的情况。
还有宫女传说,曾经见过有女子赤裸身体,背负一人,肋生光翼,冲天而起。我对这种怪谈嗤之以鼻,从没有听说谁能生出光翼冲天而起的。你当这是皇家西印度股份公司传回来的希腊神话呀?
酒宴吃的差不多了,胡监丞第一个退席,大家也纷纷表示要散席,各自寻找各自的消遣去,毕竟这些年商业繁荣,京城早就取消夜禁了。赵队过来对我耳语,意思是让我将罪畜洗漱打扮一下,悄悄送去胡监丞房中。我心领神会,就是心中有些不舒服,可能是女性的同理心吧。但是我不可能因为这点小小的不舒服而拒绝胡监丞的要求。赵队介绍过,金监正是一位武痴,已是宗师圆满,一心想要突破天人极限成就目前第二十八位大宗师,平日里他坐镇监中,不理俗物,不假女色,都是胡监丞主持日常工作,我怎么敢拒绝他?
于是大家四散,各忙各事去。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殷春桃离开后的小黑牢中,
我叫…王美香,他们说我是个毒夫杀子的淫荡毒妇,是一名养不熟的混血苗女,是一名丧尽天良十恶不赦丧心病狂灭绝人伦的死囚。随便他们说什么吧,我无所谓了。
江湖儿女江湖老,我艺不如人,身败遭擒,还连累了至爱亲朋。我哭过,骂过,埋怨过这个不公的社会,怨恨过这些吃人的权贵,幻想过自己虎兕出于柙而后复仇雪恨的故事。然而这一年多来的拷打、拘束、调教、关押让我最终认清了现实,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命运的主人,但是当历史的一粒尘埃轻轻落在我的头上,我才发现这是我永远跨不过去的一座巨山。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我们都只是命运的奴隶,不对么?
我的心中,就像是天崩地裂的灾难之后,世界已经毁灭,岩石也已冷却,巨大的火山坑中,只落下洁白的雪,覆盖住万事万物的余烬。
昨天晚上,刑部的女牢子,不情不愿地给我清洗身体,用凤仙花染红了我的指甲,再次剃干净了我的毛发。
今天早上起床后,我就被刑部大牢的捆绑手用降魔带紧缚起来,她们还用一堆污秽之物堵住我的嘴巴,用尿道锁封住我的尿路,好在未经允许没有给我灌肠。
她们用皮头套闷住我的头,让我近似窒息,如果能运转内力,我可以使用龟息功半天时间不用呼吸,但是现在只能靠身体硬抗。
她们将我装入箱中,搬运上马车,在我无聊地昏昏欲睡之际,马车缓缓开动。这是要去向何方?运送到哪儿?我都无所谓了,最好能今天就上法场,我累了,让一切早点结束吧。
马车慢悠悠地移动着,我时不时睡着或者昏迷过去,大约一个多时辰后,车停下了。
押运的人轮流去吃饭,没有人想到我饿不饿,也没有人关心我是否会被闷死。我只是一件物品,被运输,被放置,在等待新的主人。
等待是我过去一年半中的最常见的状态,被紧缚、吊起、固定在各种刑架上、打包装箱、关入各样的黑牢中。我在站立、躺下、跪着、趴着、狗爬、倒吊、反手吊、水平吊、开脚、桃缚、一字马等等姿势下,一次次地等着那个人的到来。
这一年半的时光因为太无聊又太过刺激,在我回忆中被无限拉长,仿佛亘古以来,我就一直在一次次等待他的到来。
有的时候我会陷入迷惑,更早之前的那个人真的是我么?是不是我在受刑过程中自己给自己编制出来的一段记忆?好让我觉得自己不只是一头等待受刑的母畜?还曾经是一名正大光明的人?那么我究竟是王美香么?还是别的什么人?
不过事到如今,我已经被大武律剥夺人的身份。过去的身份究竟是谁,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一头引颈待屠的畜生,谁会在乎她的过去与未来呢?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消磨,宝贵的天地灵气从箱子通风口(如果有的话)和缝隙中进入,再经过严厉封闭的头套缝隙被我吸入。我贪婪地小心翼翼地吞吐着这些灵气,维系着自己的生命,生怕有一丝丝地浪费,我还有不能死去的理由,就是有点想不起来了。
终于,我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似乎在交接我这箱物品。一段时间后,他们将我搬下车厢,再过了片刻,有人打开箱门。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灵气,看来要见到新的主人了呢。我没有好奇,没有期待,没有抵触,没有愤慨,只有彻彻底底的死心和虚无。
回忆被一阵震动所打断,我虽然内力被封,但是身体素质还在。我的身体触觉比盲人敏锐十倍,往日江湖争锋,这种触觉可以帮我提前感知危险,但是沦为刑畜的这一年来,敏锐触觉在药物的放大下,让我吃尽苦楚。
我仔细感知的这些震动,居然是有人将武道意念包含在一次次震动中来画画。这种意念太过微弱,只有我们这个层次的人才能感知,也只有我们这个层次的人才能画成功。要知道,华夏文字本身就是一幅幅小画呀!
我辨认着这些文字,组合成一句话,内容是:“新来的,你好!”每句话开始说之前和说完以后,都会传来两个强烈的空白震动,估计是我有话要说和我说完了的意思。
等对方说了三遍,我在她说完这一句后,用额头撞击面前的地板,先一步发出了自己的信息:“我很好,你是谁?”
就这样,我们隔着厚实的监房墙壁,开始了交流。
对方:“我住在一号监房,你可以叫我一号。名字在这里并不重要。”
我:“好的,我今天才进入三号房,那么我就是三号了。”
一号:“对,其实我们之间还有二号,但是她这两天心情不好,不爱说话。二号,出来跟新人打个招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