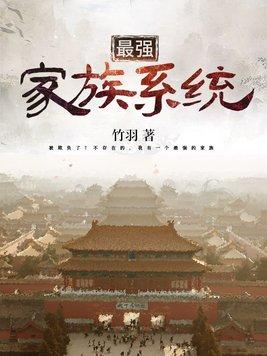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鱼龙舞(妖刀记前传) > 第127章 魂留命去奉玄幽影(第4页)
第127章 魂留命去奉玄幽影(第4页)
怜清浅不是摆着好看的花瓶,便即追上,也有教你杀不下手的法子。
他会那么说,只是想支开你们罢了。“下巴朝顾挽松处抬去,微微一哼。
龙方遂不再多言,捧着肉丹倒退而出,脚步声迅速消失在夜风里。
藏林先生垂落视线,淡然道:“你故意提到邵咸尊,是想测试我让他知道了多少,会不会威胁到你的地位。
退万步想,万一他不知道,代表我不想或不该让他知道,如今他既已知晓,我就得做出处置。“然而那小子并不知道。
顾挽松心想。
先生现身于此,那么是谁在通知杜妆怜时做了手脚,已然不言自明——运古色虽末必听龙方的指示,若教海棠在床笫间咬耳朵,挑唆他将”言满霜身份可疑“一事提前泄漏给杜妆怜,说这样便能坏龙大方的事,运古色还不跑断腿脚?龙方飓色的城府在同龄人中堪称深沉,但不惟杜妆怜涉入妖刀阴谋,连青锋照掌门”文舞钧天“邵咸尊也是共犯,肯定大出这小子的意料。
顾挽松从龙方乍现倏隐的一抹诧异中,看出形势还是对自己有利的,可怜兮兮道:“小人这点心思,何时瞒得过先生?我……我就是条癞皮狗,没了主子看管,乐得上窜下跳,忘乎所以,把东西咬破咬烂耍着玩。
但玩耍再乐,总不及瞧见主人乐啊!
龙方是年轻,但说到忠心耿耿,小人这三十多年来只有先生一个天,就算老了,不中用了,也没一刻忘记过先生。
“藏林笑道:“所以我让你交待清楚,自己犯了什么错。
知过才能改,对不?
“他一笑顾挽松心底便发寒,敢情将龙方挤兑出去是着臭棋,先生没了顾忌,不吃这套虚文应付,暗忖:“罢了,说来说去就是吕圻三这条,今儿是躲不过啦。
“此事亦在沙盘推演内,一抹眼泪收了哭声,跪地垂首:“小人贪恋吕圻三他老婆的美色,弄大了婆娘的肚子,恰巧得知那厮勾串奉玄教的龟孙子,想让先生……替我治治他,免得东窗事发,吕圻三惊觉脑门上碧油油的,来找小人算账。
“那厮素来瞧小人不起,又得先生器重,小人……甚是妒忌。
要弄死了他,先生便只倚重我啦——差不多是这般龌龊心思,才告发了他。
但吕圻三与奉玄教之人结交是千真万确的事,若无这条,凭小人也栽不了他的赃。”藏林先生微微一笑。
顾挽松心底益发没谱,看来事隔二十余年,先生听到“奉玄教”三字仍是十二万分的不舒坦。
正自忐忑,忽听藏林先生接口:“吕圻三的死真要计较,你至多出了一成力,你便末告发他,我迟早是会知道的,结果相去不远。
况且你接替吕圻三之后,差使确实办得不错,堪抵土字一系上下。
我不会说吕圻三死得好,他得如此下场,我甚是惋惜,但这并不能算是你的过错。”顾挽松如聆仙乐,连滚带爬扑前,奋力攀住藏林膝头,如忠犬仰望主人般涕泪纵横:“呜呜……先生!”藏林先生抚他手背,状似安慰,缓缓低头凑近:“但有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顾挽松愕然抬头。
“什……什么事?”
“证据。”
“证……证据?”
“对,证据。”藏林先生悠然道:“吕圻三咽气前,什么都招了:奉玄教是怎么同他接头、如何约定牵制于我,事后的酬谢等。
研究人身痛楚极限的人,末必比普通人更能忍受痛苦。
“他在崩溃之前,把一切能想到的恶毒字眼都骂完了,我才知他心里竟有忒多不满,血甲门的志业在他来看有多么伟大,乃至屈居人下,是何等负重忍辱,万般无奈。
“我当时太生气了,挽松,我是真赏识他。
直到栖亡谷内再无一名活人,我才想到忘了问他一件事。”初老文士盯着他,目光似欲攫人。
“像‘幽泉鬼医’吕圻三这种人,是无法靠言语说服的。
当然,能将一头神军缚至面前,的确胜过千言万语,但奉玄教与他勾结,远在召唤神军之前,便有独孤弋、武登庸押阵,独孤阀也没能活捉过神军。
奉玄教诸子庸碌,我料无此能耐。
“吕圻三肯定明白背叛我的风险,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又或拿到什么证据,才促使他做出如此决定?我搜遍栖亡谷,没找到这个关键之物,只能认为是被人顺走了。“顾挽松脸色微变,该不该抽手——明知是没用的——只在脑中犹豫了一霎,喀喇数响,伴随撕心裂肺的剧痛,右掌已被藏林先生捏成一团,不比一只女童抛玩的五彩沙包大上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