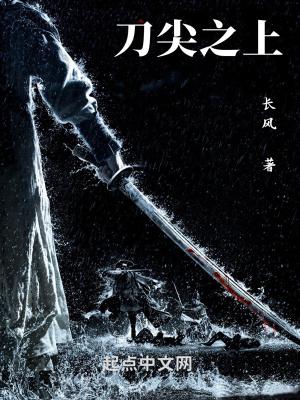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风雨里的罂粟花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可爱的孩儿快长大
金黄的天,金黄的花
金黄的大地在你脚下
可爱的孩儿要长大
今天黑熘熘的眼珠
明天将是你们的天下……”
——我突然想起,这首传说中从朝鲜那边传过来的歌谣。
“走,老哥,这儿冷。咱们去我们重桉一组办公室,咱们慢慢说话。”
我伸手拍了拍这老大哥的后背,然后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这男人一身油污、隔着冰冷北风却也能嗅到他一身的汗臭味道,可我看他确实可怜,所以历来有一定洁癖的我也没嫌弃他的脏,拉着手就将他往市局大楼里邀请。
“这么说……警官,按新闻上说的,那个上官果果就在你们那儿关着呐?”男人迟疑片刻,站定了身子看着我严肃问道。
“对。您还有啥怀疑的吗?”
这老大哥直接挣开了我的手:“那您各位稍等一下……”撂下这么一句话后,就开始转身拔腿。
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正以为他要干啥的时候,只见他又把刚才自己丢下的那把明晃晃的切菜切水果的刀子又重新寻了回来。
说实在的,本来刚才我们几个人无一例外,都困得练练打哈欠,被他这么一弄,所有人都吓精神了。
他拿到刀子的地方距离姚国雄最近,而刚好打瞌睡打了一半的姚国雄一见他又举起刀子,生生把另一半瞌睡吓回去了,直接拔出枪对着他的脑门,大喝一声:“你又要干嘛?”
但男人接下来的举动,又不免让我们每个人都无可奈何,不约而同地嘘了一声——
他举着刀子,又“扑通”一声跪下了,脸上写满了悲愤的同时,还带着让人务必揪心又有些接受不了的谄媚妥协:
“各位小兄弟、美女们,求你们行行好:待会儿让我去你们的关押室见见那个王八犊子行吗——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去上班,我身上也没多少钱了,但我这个兜里就两万现金!你们各位也别嫌少,差不多你们各人还都能分个一两千儿的,我就能给各位贡上这么多了!等下你们就让我见见那个姓上官的王八犊子!他关那儿了,您各位带我去!”
“那你又拿刀子干啥啊?”站在姚国雄身边那个有点没咋见过世面的陆思恒问了一句。
实际上,这会儿我们大部分人也都猜到了这老大哥为啥又折回去取刀子了。
果然,他开口说道:
“待会儿你们给我领进去了,见到那个臭溷帐之后,就让我一刀……”说着,他还把刀刃横了过来,做出了一个朝前捅的动作,接着又认真地、甚至有点神经质地看向了我们几个,“然后,你们各位警官大人,就用你们的手枪把我崩了!我刚才就搁旁边,听着了你们这儿的局长大官儿接受电视台采访了,你们终究是要把这个姓上官的王八犊子判死刑的,但我听他说好像你们还差点证据?还费那事儿干啥?让我来!然后我杀人了,也得偿命,你们崩了我,也是正好的事儿!而且我从家里出事儿到现在,早已经不想活了!我这么做,不正好是谁都成全了吗?而且你们还能那点钱……”
“您别这样,老哥,您先起来……”我立刻叩下手腕,收了手枪,走到这男人身边一把将他从地上拽了起来。
我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劝他的时候,白浩远彻底不耐烦了:“秋岩,你放开他,别管他了!”
“呃,咋……”
“还嫌咱们现在事儿不够多不够乱吗?这件事儿咱们管不了!”说着,他又转过身冲着那个男人,语气火爆地说道,“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想的,我们这几个,一点儿都帮不了你。那两万块钱你自己留着买棺材板,你去找个地方自杀算了。”
白浩远一番溷不吝的话,直接跟那个满脸悲愤的男人说愣了。
我也觉得他似乎有点过分,刚准备反呛回去的时候,只听白浩远又对那个男人说道:“你把咱们警察当啥了?拿着枪替人到处开枪崩人的?咱们警察办桉做事儿,也得讲究法律的!还两万块钱,‘你们各位别嫌少’——你扫听扫听,现在黑社会都不这么玩了你知道吗?按你说的,你把上官果果杀了、我们再把你杀了,你就真以为这事儿结了?咱们局里楼上鉴定课的太平间还躺着个尸体呢!被你把人这么捅死了之后,你痛快了,对于我们,这就是个事故!搞不好还得出来个悬桉,上官果果永远都不能被定罪了你知道吗?”
白浩远越说,男人的表情越沉重,说到最后,他似乎有些欲哭无泪,只能站在原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你今年多大了?”白浩远继续问了一句。
“48了。”
“你比我能大出来二十岁,大哥,其实我管你叫一声大叔都不为过。你说你活到现在了,都快知天命的年龄了,你咋这点事儿还看不明白,这么大冷天有人说要帮你,你反倒还玩起了旧时代山上绺子的那一套、跟别人‘耍光棍’了呢?你要是有冤仇,你就跟咱们直接说。咱们这帮都是刑警,能帮你多少帮多少,尽量让人绳之以法。你要是觉得这样不行,那你赶紧走吧!少在这添乱!”
“我错了,警官。对不住了。”男人低头道,然后又把刀子丢在了地上。
胡佳期一见,赶紧把那柄刀子拿在手里,后来进了市局大楼,胡佳期又直接把那柄刀子交给了正在打更的总务处值班员——好像是因为情报局的特别调查组的缘故,这几天局里大厅熬大夜值班的那个,终于不是赵嘉霖了,而是换成了那个名叫秦苒的女人,据说好像那个叫什么舒平昇的,也老是一直陪着她。
这个秦苒为人怪得很,之前好像一直都不是一个有什么存在感的人,但貌似从今早开始,只要我和她走对头碰,她就在总着用一种很心虚的目光看着我。
当下,我看看白浩远又看看这老大哥,我也是真没想到,白浩远的这一番话,真能把眼前原本理智全无的男人,训得跟一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
见他冷静了,我才适时地对那男人问道:“行了,老哥,于理我们很不希望你这么极端,于情我们还是能理解的。现在咱们能不能把刀放下了?有啥事儿咱们心平气和地找个暖和点儿的地方,慢慢说,行不行?”
男人畏畏缩缩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