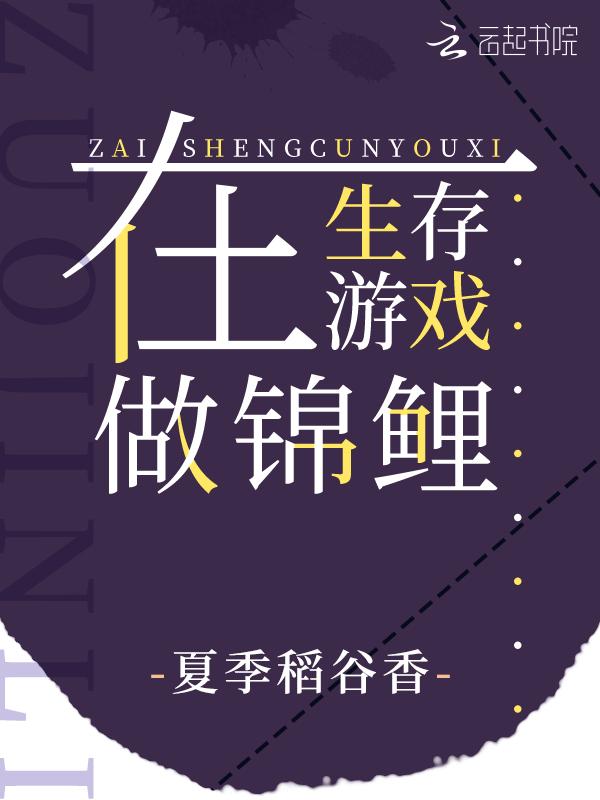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陪读母亲之熟母赵玉萍 > 第18章 检查(第5页)
第18章 检查(第5页)
“妈妈,你要帮我撸出来吗?”儿子殷切地凝视我。
“有感觉吗?”这次,我不再小打小闹,而是认真地箍住鸡巴的皱皮,上下套动几回问道。
涛涛摇摇脑袋:“不行,妈妈,还是算了。”
受伤造成的阳痿?
我暗自发问。
今天早晨,我问过儿子鸡鸡能变硬吗?
他说可以的。
叶主任检查时,也提及了勃起功能,儿子也表示勃起正常,那这会儿又是什么情况,难道儿子在骗我们?
我凑近细瞧,这根大宝贝即使像软体动物般,依然带了几分男性独有的雄浑气息,以至那刚刚尿完的骚臭味儿,刺激着我身为女性所潜藏的本能欲望。
女人的矜持多半带有欺骗性,骨子里也渴望性爱的滋润,可相比男人对色欲赤裸裸的追求,女人伪装得更好罢了。
手心里的鸡巴是火热的,我的心中也迸发了星星火苗。
我左手的掌心托着儿子如累累果实一般的囊袋,右手撸开皱皮,屏紧呼吸,朱唇在龟头上浅尝则止地亲吻了一口:“这样有感觉吗?”
涛涛摇头,立刻又换做点头。
我吐出舌尖儿,在龟头冠上轻轻巧巧地扫了一圈,抬头再追问道:“那这样呢?”
涛涛点头的样子好像啄米的小鸡,透露着男孩的可爱,也可能是在装傻卖萌吧。
妈妈不顾颜面,吃亲生儿子的大鸡巴,除了燥热的内心,还有燥热的脸颊,连裙摆内的秘处也隐隐泛着燥热。
我鼓足勇气,拢了拢秀发,拨去身背后,省得碍手碍脚,启开两瓣涂了釉彩的红唇,将半颗龟头含进唇瓣间,滋滋地吸吮,轻轻地舔舐,尿骚和咸涩夹带了男人的雄性气息,直达我的嗅觉神经和味蕾。
一个爱干净的女人,不是应该讨厌这种骚哄哄的气味吗?
我帮老公口交时,总是要警告他,事先必须给老娘洗洗干净!
否则,嗅见男人的这股子酸臭味,就令人倒了胃口,再没心情做下去了。
但儿子鸡巴的气味却勾动了我的贪婪,非但厌恶的情绪转瞬即逝,还愈发冲动地张开嘴,一股脑儿吞进整颗龟头,难道正应了那句俗话,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很快的,我便适应了这种气味,不停吞噬着鸡巴杆子,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靠近嗓子眼。
我的手撸套着皱皮,我的嘴品咂着龟头,经过这样的双重刺激,儿子的大宝贝终于开始膨胀,跳动,棒身变得硬硬的,龟头变得鼓鼓的。
尤其是龟头,在我的口腔里像充气那般,只觉得狭小的空间快要难以容下他了。
鸡巴频繁进出,青筋浮起漫布的粗壮茎身真的像烤肠般充满弹性,撑开我的小嘴,滑过我的牙关,顶开我的娇舌,然后,我用娇嫩的舌尖儿缠裹住茎身,热量激发出一波接一波口水。
我盯着尚未被我吞掉的那一截,盯着尽头那丛繁茂黑亮的男性阴毛,裙摆里隐藏的秘密在轻颤,也激发出一缕缕涟漪。
“哦……妈妈……好……好……有感觉了!”涛涛靠坐在椅子上,扭动起屁股,好像屁股被针头扎到了,身体显得僵硬而紧张,眼睛直勾勾地,毫不避讳地饱览我半露的酥胸玉乳。
我是没办法回应儿子的,只剩呜呜的闷哼声,因为我的口腔里塞满了龟头,何况他还会不时地抽搐一下,冒出浓郁的男人味儿,不清楚是龟头蒸腾的湿热气息,还是马眼分泌的咸涩汁液,与我黏滑的口水混搅作一团,丝丝绵绵地流向嗓子眼。
我逐渐意识到,当儿子的鸡巴慢慢起了变化,我需要吞掉的更多,准确地说是更长。
我越努力地吃进去,反而距离茂密蓬松的黑色荆棘越遥远。
儿子的鸡巴确实勃起如常了,可我这个妈妈却抛弃羞怯,任由欲望占据了心智。
就在裙底深处,内裤绵裆那条狭长的湿痒之地,遭受违背伦常的淫欲侵袭,钻入无助抽搐的甬道,像千万根细细的针尖似痛似酸地扎向我的骨头节,那滋味犹如受刑。
“呜……呜……”,我声如哽噎,脸腮和颧骨被浮肿的龟头撑得疼痛难忍,我揉着两粒饱胀的“橄榄核”,握着一根滚烫的“大香肠”,想更进一步,往口腔深处吞咽。
有根东西含在嘴里,口水不自觉地分泌,也许又添加了马眼口滑滑腻腻的腺液,龟头很容易顺进去,像根木棍子似的,直愣愣地封住嗓子眼。
这深吞龟头的办法,没能缓解两颊的胀痛,却反倒让我喘不过气来。
慌忙间,我吐掉了大鸡巴,连喘带咳嗽。
儿子这根恢复气力的大宝贝,紧裹着赤红的袍子,就立在眼前,全身沾满了我的唾液,好似因为侵犯了我的小嘴、娇舌、嗓子眼而威风凛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