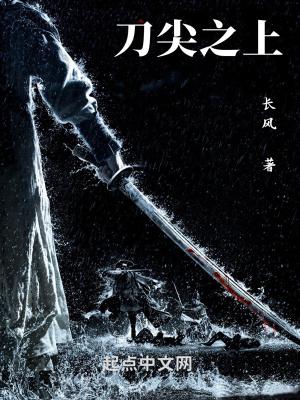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6334 > 第73章 海猫(第1页)
第73章 海猫(第1页)
皮肤直接接触是一件恐怖的事。
或许是深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东西,赤裸相贴,让人感到危险、失控,甚至联想死亡。
韦叶觉得贴着她的是个尸体。
……或者说即将成为尸体。
因为正常的人类没有这么激狂的心跳,也没有这么病态的喘息。
这是窒息前起伏挣扎的求生动作,躯体本能的颤抖抽搐,他的呻吟声满怀痛苦,又掺杂着癫狂的欢欣。
仿佛下一刻就愿意死去。
她盯着她腿间蠢动的那一团头发,这团头发下面时而露出一小片额头,肤色泛着潮红,带着湿润的薄汗。
发根都是湿的,顺着两鬓滴水,染在她的大腿上。
他吐息灼热,煎熬无比,唇瓣一次次地张开吮她,像贪食的鱼。
鱼有舌头。很长,很黏滑的舌头,舌尖柔软灵活,一次次沿着沟壑,舔进源头中。
只有喝到水,他才能不死。
“……”他说话变少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唇舌,两手揉着她的腰肢,让她坐在他脸上,前后晃动。
一次又一次,她听见潮水的声音,腿间的软肉被碾压,咬啮,嘬吸。
这房间里充满了空气。
但韦叶却感觉自己在海中,高盐分的海水托起不会游泳的落水者,强烈的失重。
水波用力推挤,将她卷进大海深处,她抓住礁石上的水草,维持稳定。
但是她依然在摇动。
水草不是水草——是人鱼的头发。
他托举她,也淹没她,让她浮浮沉沉。
滑腻的花瓣裹住他的鼻梁,也被分开两边,他仰着头追她,让凸起的阴蒂擦过他的眉心,浓密的眉毛沾了水,有些刺人,毛尖扎着软腻的贝肉,蘸取透明的汁液。
鼻尖时时滑进穴口,顶开缝隙,悄然钻进去。她的体重毫无保留,将他压扁,他只能张口喘息。
他的嘴唇在动,发不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