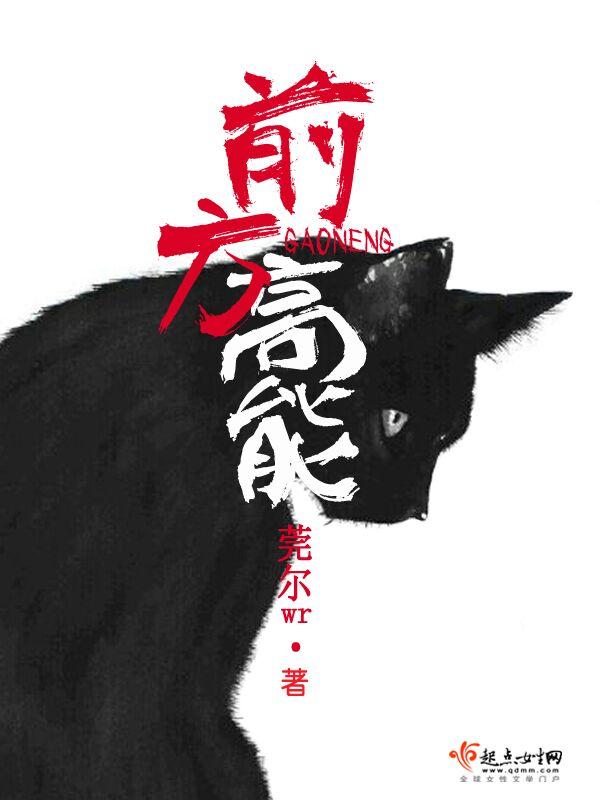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我又没让他喜欢我[星际] > 6070(第16页)
6070(第16页)
明树乐了:“哈哈哈哈哈,我哥哪有那个胆子啊?他在恋爱的时候要是有打仗的十分之一的胆子,也不至于暗恋十年。”
所以,当炽树早上睡醒的时候,他就得知妹妹连夜跑路的事情。
炽树还有点纳闷,自言自语地说:“我又没打算问责你,也没有要骂你,我有那么可怕呢,怎么逃了?”
其实炽树一夜没怎么睡。
他太太太激动了。
光是想到自己现在已经是克里琴斯的男友这件事,他就想笑,情绪波荡,根本难以入眠。
时间一到,他就马上弹射起床。
跑到克里琴斯门口守着,准备等克里琴斯一起去上班。
克里琴斯太累了,前几天消耗太大,回去以后洗了个澡,过于高昂的情绪过后,他倒头就睡。
他好像很久没有睡得这么沉,睡到起床铃响了也没醒。
炽树见克里琴斯已经超过平时起床时间十分钟还没起,心生担忧,直接刷限权进去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他打开客厅的灯,放轻声音呼唤了一声:“Coti?”
没有人回应他。
卧室门半掩着,炽树走过去,摸到墙壁上的开关,打开光线较为柔和的床头灯。
克里琴斯正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睡觉,几乎把整张脸都埋在了被子里面,只露出一点额头。
炽树又喊了一声:“Coti?”
被子里跟毛毛虫一样的人形动了动。
炽树怕吓到他,不知道要不要离开。
不知是不是听到了动静,克里琴斯探出头,睡眼惺忪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继续睡了。
炽树走到床边,蹲下身子,再低头,视线与躺着的克里琴斯齐平,温柔地问:“很困吗?要我帮你请假吗?我可以帮你分担工作?”
克里琴斯皱起眉,显然是挣扎着慢慢醒过来了,他的嗓子有点哑:“不用。”
又问:“几点了?”
炽树说:“八点十三分了。”
克里琴斯扑腾了一下,尝试起床,平时都能成功,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缺乏力气,他先把脸从被子里完全探出来,整张脸都红扑扑的,脸颊上还有一道枕头压出来的印子。
克里琴斯说:“这么晚了?我该起床了。”
声音还是哑的。
炽树很自觉地说:“我去给你倒一杯水喝。”
克里琴斯便干脆再眯一会儿了,一不小心差点又睡了过去,炽树当他是个小孩儿似的,直接把他半抱起来,吸管都给他准备好了,他可以躺着喝水。
克里琴斯并不客气,就这样躺着被伺候。
炽树见他都钻出来晾了晾脸蛋,但是绯红不减,心里觉得不妙,摸摸他的脸颊额头,叹气说:“果然发烧了。”
难怪他觉得身上特别不舒服。
克里琴斯想。
但他反而股足了劲儿要爬起来,他已经旷工那么多天了,不能再请假了,不然也太不像话了!
克里琴斯强硬地说:“去给我拿点退烧药。”
炽树把人按回被子里:“你都生病了,请假吧。这些年,你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因为私事请假,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把以前十年攒下来的假期用掉,没有人会指责你的。”
克里琴斯说:“不是会不会被指责的问题。”
“你正常上班了,我生病没去,那我成什么了?”
炽树头疼起来,各种意义上,他都希望生病的人是自己:“那我也请假,我们一起不上班。反正这几天没什么事。”
克里琴斯梗着脖子:“那我们都不是上班,他们肯定以为我们在谈恋爱。说不定还会想些有的没的……”
炽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