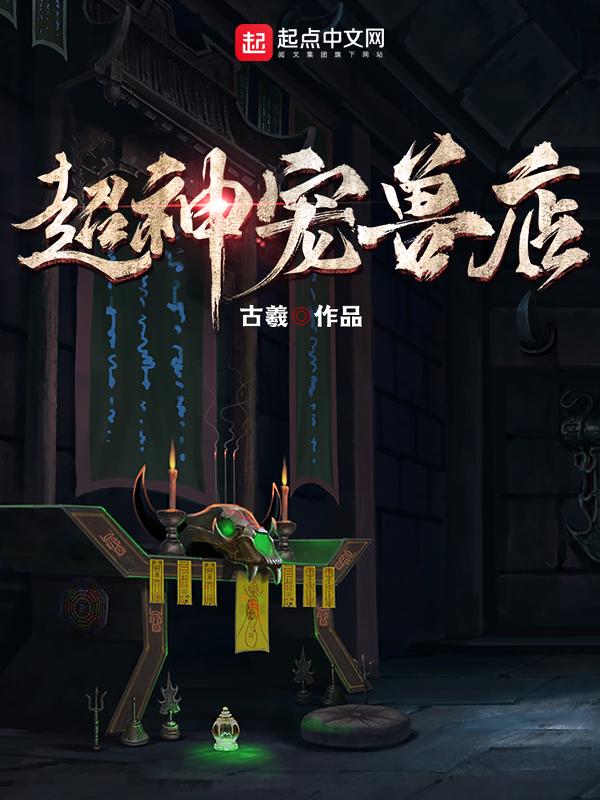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为药 > 完结番外(第23页)
完结番外(第23页)
不然凭什么在岑人的力量逐渐衰减的情况下,她岑姣偏就不一般,不光能够御兽,甚至可以轻轻松松地御蛟呢?
岑姣可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幸运之子,是颓势下的异类。
所有的不寻常,一定都是有迹可循,是旁人的机关算尽。
被人当作棋子的感觉,不好受,岑姣也不喜欢。
只可惜,面对执棋的人,岑姣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她捂着胸口的位置缓缓站了起来,抬眼去看,是苍茫的白色。
玉制的佛头随意丢在地上,堆在两侧,杂乱无章。
岑姣走动时,心口的位置扯得微微有些疼,她感觉自己应该是死了,没有人能够在心口被贯穿后,还能好端端地站起来,除了有些疼以外,没有半点不妥。
起初两步还有些趔趄。
到后面,岑姣便已经松开了手,她抬脚,快步朝着前方走了过去。
两边的佛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到后面,那些佛头东倒西歪的,眼睛却又纷纷看向岑姣,无端平添几分诡谲。
岑姣的手垂在身侧,她看向了视野尽头。
那是一棵白色的树,虽是白色,可岑姣却又觉得,那该是青铜铸成的树,树干枝条上,该有着青铜的疮疤。
岑姣停下了步子,在那棵白色的树下,有一个人坐着。
是个女人,披着长发,不着粉黛,穿着麻布的裙衫,光脚踩在地上。
可是岑姣有些看不清她的脸。
分明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遮挡,可是岑姣就是看不清那个女人的脸。
女人坐在树下,她左手握着一块木头,右手捏着一把刻刀。
随着她的动作,木屑飞舞。分明没有风,可那些木屑却像是翩跹的蝴蝶,飘在半空,围绕在女人的身边。
岑姣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她看着那个女人,没有说话。
她看不清女人的脸,也确信自己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女人,可是偏偏岑姣心里对女人的身份有了肯定的答案。
岑人的一切来源于岑祖。
没有人知道岑祖来自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她一身的本事从何而来,甚至于连岑祖的死亡,都显得奇怪又瑰丽。
传言里,岑祖陨落那日,山河移转,沧海桑田。
这样一个人,一个能够影响岑人那么多年的一个人,当真会那样死去吗?
岑姣不确定。
她盯着面前的人,略有些出神,或许当年,岑祖的确死去了,可死去的只是那一具□□。
女人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木雕,她朝着岑姣的方向看了过来。
她的脸上有五官,可那五官上方,仿佛蒙上了一层薄雾似的,岑姣怎么都看不清那张脸。
“过来。”女人开口道。
她的声音有些空灵,仿佛是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岑姣的耳朵里,那声音让她一个激灵,浑身的寒毛都随之竖起。
岑姣抬脚,往树下走了两步,只是刚刚走出去,便又下意识回头去看。
在她身后,那片白色苍茫被染成了红色。
那红色,是鲜血的颜色。
岑姣的指尖轻轻颤了颤,她看向自己垂在身侧的手,她的手掌一直在淌血——即便没有伤口。
树下的女人,似乎也移转视线,看向了岑姣垂在身侧的手。
只见她缓缓站起身,走到了岑姣面前。
像是山脉之间的轻风冲着岑姣的面庞吹来,岑人生来便与土地亲近,所以那微凉的风并不让岑姣觉得奇怪,反倒让她生出几分亲近之意。
只见女人停在了岑姣半步外的地方,她抬头左看看,右看看,似是在寻摸些什么。
只见她抬手,从头顶的枝干上摘下了什么。
岑姣看向女人的手掌,那像是树上长出的果实,又像是一团泥土或是一朵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