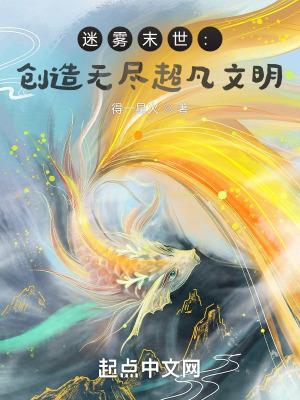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我家徒儿总想弑师 > 8090(第7页)
8090(第7页)
天色越来越凉了,那月亮不怎样配合,想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出来了。
颜华池起身,把熟睡的人抱起来,拢在怀里,“您要乖……”
他将人抱紧,往里屋去,“师父要是不听话,徒儿就不顾忌那么多了,徒儿折腾得您以后都别想睡了……”
沈长清在睡梦中蹙眉,像是不满徒弟这大逆不道之言。
午夜,月亮终于穿透云层,照在沈长清脸上,给他蒙上一层薄纱。
“除夕了”,颜华池把他放在榻上,褪下衣衫,拥他入眠,“答应我,要睁眼……”
“至少陪徒儿过个年……”
沈长清这大梦一睡,到午时方醒。
他睡了有多久,颜华池就抱了他多久,脑袋深深埋进他颈窝,倒有些……耳鬓厮磨的意味了。
手指轻轻滑过光洁细腻的皮肤,指尖残留着些微温热,沈长清又叹息起来,“又不穿衣服……天冷……”
叹息到这就戛然而止了。
天冷了,小徒弟这是想用肌肤相亲的体温给他暖热么?
傻孩子,死人怎么暖的热?
“不早了吧?”沈长清隐约感觉自己睡得太久了,有些担忧道,“今日有宫宴,颜平没让人来传?”
传了,被他甩出门外的荆棘吓走了。
这些他自然不会告诉沈长清,“不管旁人的,您还有话没跟徒儿说……”
沈长清愣了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已经除夕了。
心中忧虑太多,下意识忽略节日都是常有之事,沈长清眉目渐渐染上笑意,“罢了,照例该你先的……”
“新年……快乐”,沈长清翻了个身,“不止此年,往后经年,为师的小哭包都要快乐。”
颜华池把脑袋凑过去,在沈长清唇角印下浅浅一吻,“早安,不止今天,往后每一天,都要您永安。”
沈长清沉默着,把小徒弟搂紧,直到又一位新的小公公抖着嗓子喊他们去赴宴。
今日之后,或许便是永别……
沈长清将颜华池抱得更加紧,语气里罕见地带了不舍,“你去北域,事事都要小心,唯一能信任的,只有余字号的人明白吗?”
就抱了一小会,他便松开手,慢慢绕到屏风那边,给自己换了一套衣衫。
仍是青白的配色,只比以往要繁琐许多,身上流苏穗子数不胜数,腰间环佩叮当作响,长长的白发梳起来,用青玉束好,脑后坠了两根细细的发带下来。
这套衣服他穿得很熟,曾经做国师时,最常用的就是这样的制式。
那时候常常要接待他国的使者,最初的时候还要人伺候着,后来渐渐熟悉起来,每一样饰品该添在什么位置,都烂熟于心。
每一道纹路,摸过去,就知道该怎么处理。
瞧着与三千年前并无什么不同,只是下意识捻起手指时,才发现少了样物件儿。
年少时颜柏榆在通灵寺虔诚求来的菩提串儿、心寒离去时宫道上散落一地的翠珠儿、死后萦绕不散的执念用他心魂化作的青白渐变的手持……
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留不住的结局。
三千年岁月不过是黄粱一梦,那些模糊了的记忆,不再清晰的脸庞,只能在半睡半醒的时候怀念怀念的过往……
都早逝去了不是吗?
沈长清把广袖捋平,手藏进宽大的衣袖里——从穿上这一套衣裳起,他便不再是沈长清,他是天齐的国师!
那些刘元青用疼痛一遍遍反复刻划在他潜意识里的仪态、规矩,在这一刻发挥了莫大的作用。
他将脊背挺直,目光平视前方,端庄迈步,嗓音温润儒雅,语气柔和,礼度恰到好处,“走吧,跟好。”
颜华池心神一荡,手指捏着自己绣了金线的白衣,不由自主就听话跟上。
沈长清这人啊,他有种伟力,他就像春雨,润物细无声,而旁的人就像种子,很自然接受他那温柔的侵入。
会敞开心扉,会下意识按着他说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