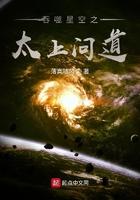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春厢秘史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人都说是冤家路窄,越躲越来。
人生在世可不正是如此:你想见的,遍寻不着,怕见的,倒上赶着来找你。
上章说到道这赵玉庭在桌席间与朋友吃酒取乐,不巧真就遇上了白信。
这赵生此刻心里头的念想煞地分做了两半儿:一半儿如干柴遇了烈火,噼啪直着;另一半儿又如耗子见了大野猫,只想落跑。
他这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许久才憋出句客套话儿来:“久仰久仰,在下赵赵赵赵赵玉庭。”两旁损友看这架势,自是逮住了机会又拿他取笑:“赵兄怎的结巴了?想来是迷上了白兄这美姿容、好样貌,话儿都说不齐整了。”赵生驳道:“你们几个少来胡闹,倒叫白兄看了笑话。”说罢自顾吃酒,以掩心中惴惴。
如此这般几人又像上午一样吟诗作对,间或行了几个作赋的酒令。
一顿下来那白信是谈笑风生举止如常,这边赵玉庭却是如坐针毡手足难安。
好在后来白信再没与他说话,眼神儿也没碰过一回。
赵生才安下心来。
吃罢酒菜,几个朋友照白信的提议去租了小船儿游湖,赏花戏水,顽了一个下午,也都是尽兴。
其间赵白二人仍是并无交流。
直到天色见黑,几人又找了间小店进去吃晚食。
刚坐定了,一人问道:“昨儿个我见南城有家妓馆新开了张,里头景致摆设不似平常勾栏的富丽,却是雅致非常。几位可有兴致一去否?”其余人纷纷应了,却见白信道:“小生倒是想去,只可惜今晚另有佳人相伴,恕难相陪了。”众损友自是又念了一番淫浪话儿,白信也跟着接上几句,嬉笑快活。
赵玉庭适才想起那张约了今晚见面的纸条儿,有心示意白信,却见他望也不望自己一眼,不知心里是甚么念头。
赵生心里边儿是活泛着有些想去见他,更多的却是怕去。
心下道:我若应了几位朋友,便准能躲过今宿这一劫,不再搭理这扫把星去。
于是张口欲答应同朋友去那妓馆。
正在这时忽觉得一双脚勾上自己腿来,上磨下蹭,缠缠黏黏,好不淫亵。
赵玉庭假做拾筷子往桌下一瞅,可不正是那白信作的怪。
他这边愈挣,那边缠的愈紧,俩人在桌底下来来往往缠闹了几个回合。
恰逢此时一个朋友问赵玉庭:“赵兄你呢,可与我们同去?”赵玉庭有心说不去,适时却有桌底下一只脚,正拿着巧劲儿来磨他裆处,弄得个赵生丢盔弃甲投了降,只得回那朋友道“我今儿晚上要回去听家父训话呢,便不陪你们了”,支支吾吾混了过去。
几人说说笑笑又吃一阵,已近了亥时才各自散了。
赵玉庭被桌下那一对不老实的足闹得厉害,起身时直要腿软,最后强自站定了才走出门去。
横竖是快要到与那人相约的时候了,赵生索性捡了小道直朝撷花院走了去。
白信就在不远处缓缓跟着,也不来与自己说话,赵玉庭心里有些恼他,却不能发作。
再说那白生,眼瞅着赵在前头别扭,便成心要吊他胃口,一路远远跟着。
直至快到了撷花院,才三步并作两步撵上,去拉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