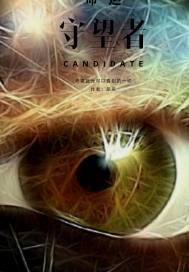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她,一心修仙 > 180 第178章 序章 前世因(第3页)
180 第178章 序章 前世因(第3页)
听到这句话,他从悲思愁绪中抽离出来,问道:“那得如何?”
谢怜托腮皱眉,认真思索起来。
小女子年龄虽小却总能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望着苦思的谢怜,他不由也托腮冥想。
“噫,要不磕了头再走?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她终于出声,对上他认真凝视的眼时却胡乱挥起了手。
“不晓得,不晓得,我不会写故事。”
他不由失笑,这小女子分明揣着聪明装糊涂。
“小女子你终日跑来看话本子,家中亲人不担忧你?”
他还是耐不住疑惑,问出了声。
她小声地说道:“我是钻了狗洞偷偷出来的,这话不足为外人道也”
她一本正经地学着他书中的句子,古灵精怪的样子倒像是一只偷油小鼠。
“呀,天不早了,要赶在爹爹回家前回去。”
她起身跑开两步,复又转头。
“以后叫我小友就好。”
挥手便跑开。
“小友。”
他咂嘴,随之笑了,他们年龄相差甚远,她于他确是小友。
深夜犬吠,风雪归人。
骤降的雨雪让他措手不及,手忙脚乱的拾掇中,身边风雪乍停。
他抬头望去,原是日日蹭书的忘年交举着伞来了,不过近日她低垂着眼,不似往日欢快。街角的茶铺里,寒风扯着门帘一下一下摔打在门框上。
谢怜捧着茶杯,倔强地忍着泪。
门帘不堪重负终被扯落下的瞬间,狂风夹杂着不胜悲苦的呜咽袭来。
之后再见到她时,已是几个月之后。
那日正值初春,二月二,龙抬头。
隔了一冬,万物都跟着春光泛了活。
他深受赶着树下飞虫,再抬眼时谢怜已站在了面前。
“小女子少不更事,常扰先生清幽。”
纤纤素手捧过一只绣袋。
“心有歉意,还望先生原谅。”
他还没来得及委托。
谢怜已继续说道:“经此一别,怕是再无相见之日。”
他听完良久无言,接过东西的同时伸手从怀里拿出一卷书,郑重相赠:“无以为报,与友一书,名为《禹鼎志》”
她轻轻施礼,道:“珍重。”
“保重。”
他退一步,长袍轻揪,行的是文人相会之礼。
知己难觅,背影渐远,恍惚间他又回到了那个雪夜。
从谢怜断断续续的言语中,他才知道她为官的父亲在朝政洗牌中被剥权投狱。
至此,树倒猢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