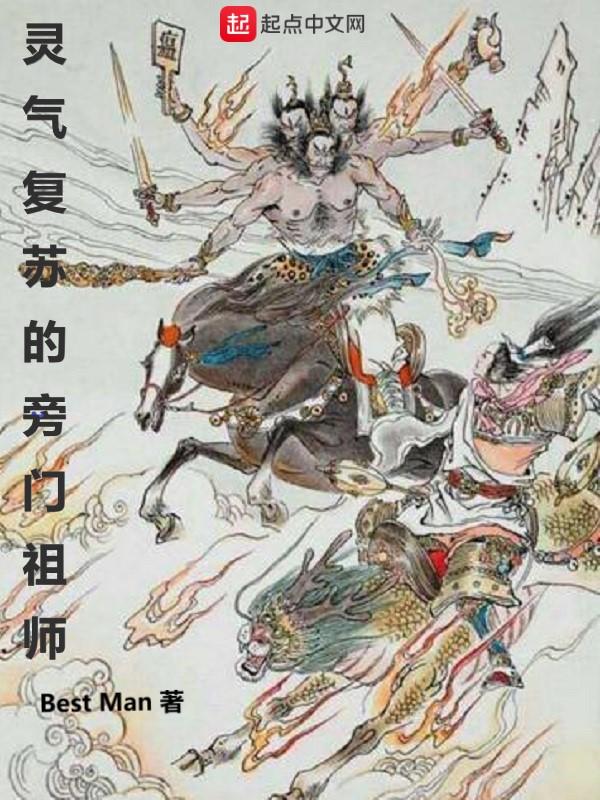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反派他不想被救赎[快穿] > 130140(第19页)
130140(第19页)
阻止他自我放逐,恐怕必须要下一剂狠药。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忽然缄默起来,他连呼吸都很轻。在他背后,是相府种的一大片树林,树枝在夜色中隐秘地交叠,树叶在轻风中悄无声息地相互摩梭,风顺着吹,直到将楚怀存身上清淡的熏香味吹到季瑛的身前。
他忽然无法忍耐地低下眼睛,甚至背过身去。
“我死以后,”季瑛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笑意,却颤抖得不像样:“看在这一场交情的面子上,楚相不至于连收尸也不愿意吧?”
说这句话时他又往反方向走了几步。他的靴子也已经探了一半进那片沉甸甸的黑暗中,但另一半却无论如何也动弹不得。
季瑛迫切地想要等待一个回答,“不可以”会让他死心,至少这一切都断绝得干干净净;“可以”则会让他感到一点从灵魂深处的慰藉。他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凭什么连这一点宽慰,也不肯给他呢?
楚怀存却很轻地笑了一声,仿佛在夜色中听到一声微不可察的冰面碎裂声。
“季大人只敢在死后嘱托我吗?”
他的声音终于也带上了一点属于季瑛的讽意,“若我说愿意,是不是会让你觉得死的特别畅快,连忍耐痛苦也被赋予了意义?季瑛,我还是那个意思,这是你做选择的最后机会,假如你退出,我不会再顾念和你的任何关系。”
季瑛的背影又像是无法维持住平衡那样晃了晃。
楚怀存在他身后无声地叹了口气。他不想扮演恶人的角色,但也不想真遂了季瑛的意,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得知一个佞臣人人称快的死讯。
他是个精湛的捕猎者,熟练地把握着猎物的每一丝颤抖,风会将对方的情绪带给他。
就比如说现在。
他知道季瑛的情绪就像是被压满的弓弦,一弯战栗不止的弯月。
“季瑛,”
楚怀存让自己听起来镇静,他咀嚼了一遍这个名字,
“我查过你,但你的消息埋得太深了。你表面上的身份站不住脚,从前年开始在陛下的直接授意下介入朝政,随后一路青云直上。你身上有用来控制人的毒,还有不得不顾忌的东西。你因为某些原因接近我,心悦于我,是什么让你忽然想要退缩——”
“够了。”
季瑛的声音忽然疲惫地响起来。他站着没动,还是没有踏出那关键的一步,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楚相,你以为你知道了一切事情就会变好吗,假如我说出来,我就能得救吗?”
他转过身。楚怀存的呼吸一窒。
他第一次看见季瑛脸上满是泪痕,在明亮耀眼的月光下,这一切如此毫无遮掩又如此震撼人心。
季瑛无法忍耐地直直盯着他,他们间的距离是他方才后退的距离,但他再次折返的速度却很快。几乎只用了几秒钟,季瑛就来到了楚怀存的面前,他的眼睛红了,那头黑发被月光浸泡得湿漉漉的,就像是从湖中爬上来的恶鬼。
楚怀存没动,任由季瑛恶狠狠地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两人的攻势一转,季瑛偏执地死死钳住楚怀存的肩膀,踮起脚尖,让他们的眼睛尽可能地彼此靠近,目光一瞬不移地钉在楚相眼中,吐息又湿又热,就像是一团烧起来的火焰,燃烧在他一片潮湿的眼睛里。
他们贴的很近。
楚怀存见缝插针地想了想,这显然违背了季瑛曾说出口的准则。
季瑛不声不响地就着这个亲密无间的姿势打量了楚怀存一秒钟,他显然豁出去了,哑着嗓子逼问:
“楚相,你认为这样就能把我救出来吗?只需要给我解开中的毒就不会有问题,只要在公开场合不暴露和我的关系,私下里就能拉拢我作为你的势力;只要给我折一枝花,我就会像一个傻子一样将所有的爱意尽数倾诉;只要你愿意帮我,就一定能给我救赎——”
“不,”他的声音中逐渐夹杂起压抑的呜咽声和数不清的痛苦,
“不能,仅仅是这样远远不能。我不该对任何人说,尤其是你。你还不明白吗?你不可能救我的。”
他的情绪来的太过于猛烈,脸上的泪水在月光的照耀下,就像洁白的贝母。他用了他最大的力气,楚怀存能感受到他用力弯曲的指节,那些指节在他的肩膀上留下印记,而他此时的距离简直比那次亲吻还要近。
楚相停顿了一下。
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顺着对方的姿势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季瑛的瞳孔猛烈地颤抖了一下,他偏了偏头,似乎想要像抖落一片叶子般抖落楚怀存的手,但这无济于事。刹那间,他维持到现在神志溃散得一塌糊涂。
高烧还没有好,季瑛想。但他们都心知肚明,这不是高烧的问题。
就在那摧枯拉朽的一瞬间。
楚怀存感受到一个湿漉漉的脑袋抵住了自己的前襟,他痛哭起来。季瑛的手也从钳制他的肩膀,到死死地拽住他的衣领。季大人身体不好,手无缚鸡之力,根本没有那样的力量,楚怀存不费任何力气就能挣开他。但他并没有动,那双总是如冰雪般淡漠的眼睛也被连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刺痛所取代,仿佛被一团火烧灼。
这个背负着累累骂名的人,他想,他的眼泪也是滚烫的。
眼泪就这样就着楚怀存雪白的衣襟一点点渗进去,弄脏了楚相千金难买的上好衣袍,那是无数个绣工昼夜赶出来的,暗色的纹路随着动作流转着。泪水隔着薄薄的布料浸湿了他的胸膛,心脏在偏左一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