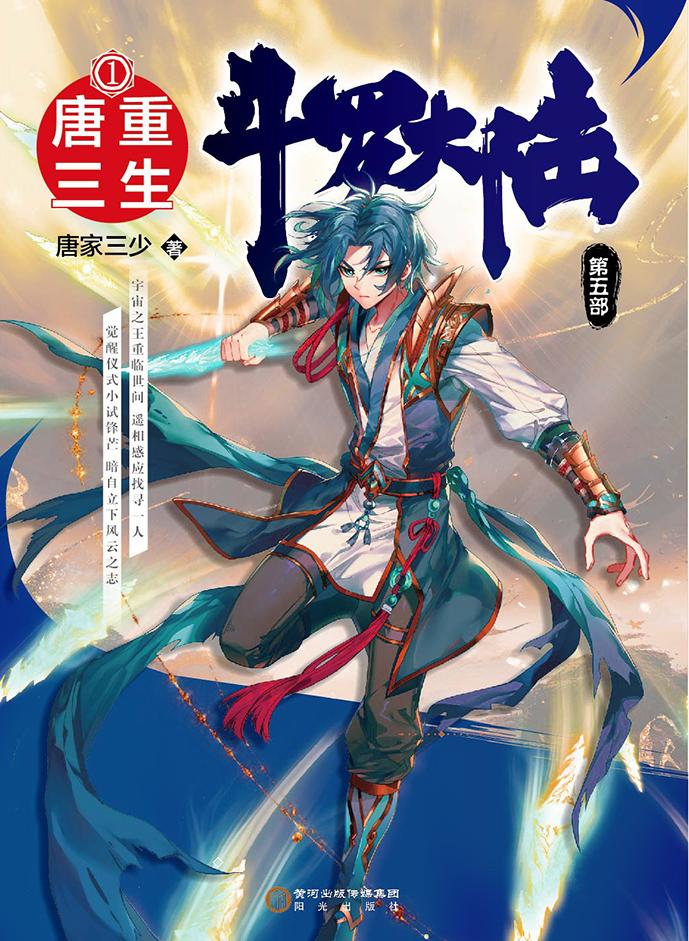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玛丽苏进行时 > 7074(第2页)
7074(第2页)
真是人至贱则无敌!
越想越恼怒,他平息不了这股郁气,果断冲上去扯断那条眼镜腿,再忿忿不平地将整副眼镜砸到地上,接着一拳打得郗时半边脸都凹陷下去。
郗时一下子站不稳,摇摇摆摆着后退了几步,最终一脚没踩稳摔了下去。
看他狼狈不已,秦方好总算吐出一口闷气。他扯了扯嘴角,神色间带有几分讽意:“真是不好意思,刚才的我太生气了,想必你一定能理解,也不会怪罪我。毕竟是你说的——”
“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
“你要怨就怨刚才打你的我好了。”
“你——”
郗时不觉哑口无言。
失去眼镜使得他视线雾蒙蒙的,原本清晰的景色都变成了大块模糊的色块,连人脸上的五官都没有了轮廓与界线。他忍着痛开始眯着眼睛在地上摸索,直到一道声音从头顶响起。
“什么东西?嗯?谁的眼镜?”
“是我——”
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只听见“咔嚓”一声,黑色的皮鞋粗暴随意地将眼镜彻底踩断,然后轻慢地用鞋尖踢得远远。
“真碍事。”对面那个人咕噜道。
手指渐渐蜷缩,用力掐着掌心,又不知不觉攥成拳。
那副眼镜之前已经修过了,不过镜框没坏,是镜片碎了。就是那天符彧带他出去的晚上被人打碎的。放在之前,他早该丢了换副新的,可因为有了和符彧共同的回忆,这就不再是普通的眼镜了。
再有下次能和符彧单独出去的机会又能有多少呢?尤其他本来性格就不算讨喜,更不如路维安他们会哄她高兴。
郗时的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缝,酸涩的心情不断发酵膨胀,几乎要撑满整个胸腔。
他用力闭了闭眼睛,并默不作声地爬起来。
然后迎着段危亭充满疑惑的声音,一脚踹向了他脆弱的裤。裆。这一脚力量非比寻常,几乎灌进去他六分迁怒、三分委屈,还有一分茫然无措。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哪个角度最容易鸡飞蛋打!
果然,段危亭登时瞪大了眼睛,满脸悲愤震怒地捂住了裆——这已经是他第多少次被精准扼住命运的要害了!为什么又是他?!凭什么总是他?!
什么时候是个人都能打他了?
被符彧拳打脚踢就算了,他技不如人、打不过,他认!
可这些男的算什么东西?一群跟段危楼差不多年纪的老东西而已。
男人二十五已经是走到了花期的末尾,三十彻底衰老,四十可以收拾收拾准备让贤纳小,五十就该自觉打好棺材养老,六十半个身体预备入土不拖累一家老小。
而他们四舍五入一下都是三十的人了,四分之一段身体埋在棺材里。再四舍五入一下,已经该入土为安了。
为什么还有脸又争又抢?为什么?!!!
段危亭气得咬牙切齿——是可忍,孰不可忍!
“梆”的一下,他想也不想一头撞了上去。
脑门对脑门,比的就是谁颅骨更硬。对于这一点,段危亭颇为自负。谁老谁丢人!刚成年的脑壳起码还有六成新,三十岁的脑壳就只剩下五成新了。
他绝口不提那一瞬间的冲撞让他两眼直冒金星。
郗时吃痛地按住前额,略微缓了缓神,便沉默地扑了上去与他厮打起来。在扑上去之前,还不忘顺手将看好戏的秦方好拖入混战。
“松手!”
“你先松!”
“你爹的!谁又踹了我裆?嘶——”
“砰!”
“都说了不许打我脸!”
“做梦!打的就是你的脸!”
“……”
叫骂声不绝,飘飘摇摇地顺着风被卷到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