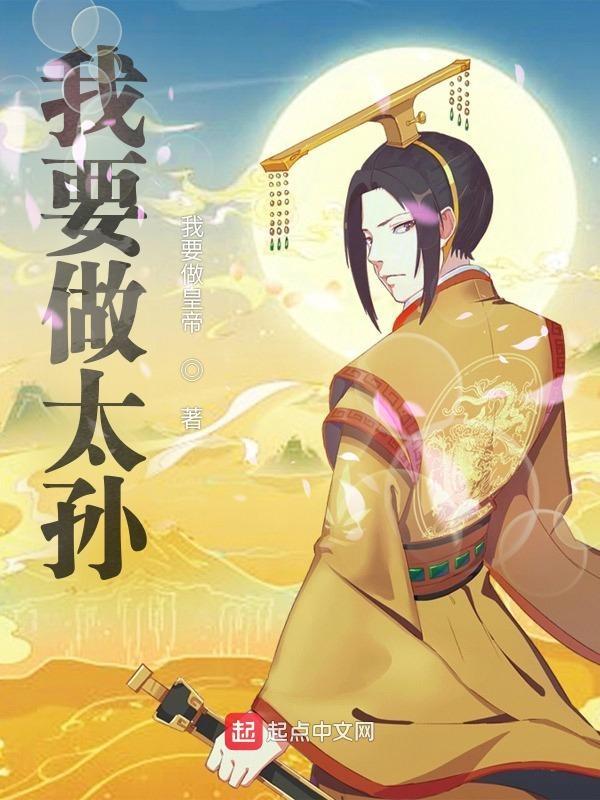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破笼 > 6065(第12页)
6065(第12页)
他这是怒了,怒了好啊,从前她便是太怕他怒,才会万般讨好乖顺,让他享受其中,如今,该是他怒的时候了。
晏翊越怒,宋知蕙脸上笑意越深,继续道:“从前我始终想不明白,你为何这般对我,为何不愿将我放过,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你,我到底何处做错?我已是尽可能去讨好伺候,可你为何还不满足?”
“你是大东位高权重的王爷,是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贵胄,要什么样的人没有,为何偏要纠缠与我?”
“如今,我想明白了,”宋知蕙朝晏翊嗤笑一声,“一个疯子的想法不重要,错的人是你,而非我,我要做的不是逃避,而是解决。”
“赵凌已死,王良已死,杨心仪,还有谁能将你带走?”晏翊虽怒,但还是松了几分力道,“纵是还有谁,来一个孤杀一个便是。”
宋知蕙又是一声冷嗤,“我自己啊。”
“你?”晏翊松开了她身后的手,随意抓起一只软弱无骨的手,放在鼻尖下细细嗅着,“哦,孤忘了,你还有那游水的本事,那你觉得孤日后可还会中你的计?”
宋知蕙笑了笑,抬起另一只手,从他唇瓣缓缓往下,指尖划过他脖颈,喉结,最后停至心口处。
“你忘了,我如今不逃了,我是要杀了你的。”她说着,用指尖在那心口处不重不轻地点了一下。
晏翊眸中泛起一股沉沉寒意,那久违的压迫感充斥在整座池房内,他一把握住身前的手,“这世间没有孤驯服不了的,若无法驯服,那孤便将其杀之……”
说着,他冷冷弯唇,“是你杨心仪走运,孤舍不得杀你,那便唯有将你驯服,若一年不够,便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或是三十年……孤有的是时间与耐性。”
宋知蕙脸上未有半分惧意,也冷冷勾起唇角,“你能活到那时在说吧。”
此话一出,晏翊又是一只大掌便将她双手紧紧钳在身后。
两人不再言语,只那水面上的波纹在不住晃动,到哪即将登顶的至极之时,哼咛了许久的宋知蕙,忽然低颤着唤了一声,“轻点……世子……”
晏翊脑中瞬间嗡了一声,所有的动作都在此刻停住,那怒意只刹那间便填满了胸腔。
迎着他盛怒的眸光,宋知蕙那微红又迷离的双眸中,带着几分嘲弄的笑。
她自然知道说什么能刺痛他。
那怒火中烧的晏翊,却是忽然勾起了唇角,“这般激怒孤,看来是你今日想要得厉害了?”
宋知蕙唇瓣勾着,细眉却是故意蹙了一下,“从前忧心王爷怒极将我伤了,如今我已不再畏惧,索性就说些实话吧,你不如赵凌的。”
“是么?”晏翊狠狠又一下,“孤记得你二人初次时,他不过是个十六七的毛头小子,那小鸡崽子一样的身板,怎能与孤相比?”
再者,晏京所送的书,他已全部阅完,他不信那赵凌能强过他。
宋知蕙吸了口气,那双眼更加迷离。
见她如此,晏翊脸上笑意更浓,心中便更加笃定宋知蕙所言只是为了气他,“孤若当真不行,你会泛滥至如此地步?”
“杨心仪。”他敛起笑意,又是一撞,“收了你这些心思,若你下次再在此时提他,孤便亲自将他刨出鞭尸,或是直接放你床畔,让他与你同眠如何?”
说完,他将她车行地翻过身去,他们之间太过熟悉,熟悉到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能让她沉沦其中,而他也沉沦在了这一圈又一圈的水波中。
入秋后,宋知蕙身体渐渐康复,如今不必人来搀扶也可自行走路。
越是如此,晏翊将她看得越紧,宋知蕙自然还是不肯乖顺配合,不论当着何人的面,她只要想起来了,便扬声骂他。
从最初听到畜生时心头会怒,到现在一连听了数月,晏翊仿佛已经习惯一般,只淡淡看她一眼,神情没有半分异样。
有时候她见他如此,便会故意一连叫上好几声。
晏翊见她怒骂时急红了脸颊,反而还会弯唇轻笑,甚至有一次当着刘福面,宋知蕙骂他时,他还饶有兴致地回应她,“好啊,孤是公畜生,你是母畜生,你我刚好凑成一对,再生个小畜生,不是更好?”
这话听得刘福落下汗来,赶忙就退了下去。
宋知蕙也是一愣,没想到晏翊脸皮竟已经如此厚了。
入冬那日,晏翊在书房处理公事,待回寝屋时天色已沉,刚一掀开帘子,脚步还未彻底迈进,便见宋知蕙立在桌旁,拿起手中水杯朝他身前直直砸去。
晏翊眼疾手快,抬手便将那水杯握在掌中。
宋知蕙又拿起一个砸他,他再次用手抓住。
随后又是花瓶,晏翊稍微侧身就能躲闪开来。
她仿若还不死心,看到什么便扔什么,所有东西都是朝着他心口处而来。
砸到最后,屋里实在没有什么顺手的物件能再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