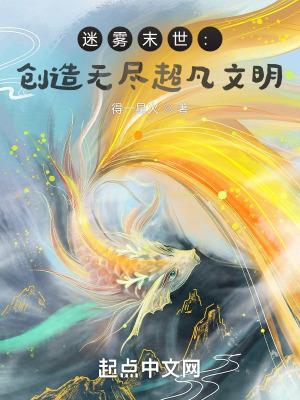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破笼 > 4050(第4页)
4050(第4页)
宋知蕙连忙再次谢恩。
晏翊那眸光却是忽地沉下几分,望着她半晌不语,这眼神看得宋知蕙后脊发凉,垂眼不敢与他直视,待片刻后,他沉冷出声,“你今日做得很好。”
这话明显意有所指,宋知蕙却故作平静道:“谢王爷夸赞。”
“哦?”晏翊冷眉微挑,“那你可知孤何故夸你?”
宋知蕙这次没有避他眼神,而是抬眼与他直视道:“虽高山难越,但妾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最终还是到了山顶。”
晏翊没有说话,而是抬手捏住了她下巴,冷冷端倪着这张脸,就如他隐在暗处,望着她与那赵凌时一样。
山崖越高,摔得越惨。
所以他想将这出戏放在山顶,偏她不够争气,这身子骨弱到只能上至一半,但这一半的高度也足以让二人尸骨难辨。
他那袖箭在赵凌出现的刹那,便对准了宋知蕙的头颅,那赵凌自有人去杀,但宋知蕙今日便是要死,也必须死在他手中。
在看到赵凌俯身而上时,那袖箭几乎已要飞射而出,却是在下一瞬赵凌被推开后,晏翊手中力道瞬间收起。
那一刻,他不知为何心头沉闷倏然松了大半。
尤其看她一次又一次躲开赵凌,一声高过一声地推拒不从,晏翊那沉到极致的面色上,逐渐浮出了一丝轻笑。
晏翊将她下巴松开,用手指在她额头正中的位置上,不重不轻点了两下,“孤忘了,你向来才智过人,不必有人点明,定也能猜出孤所指何事。”
宋知蕙手心已彻底被冷汗浸湿,面上却还是带着几分淡然笑意,“王爷带妾来爬山,不就是想要考验妾,看妾可否能有这份毅力?”
还在与他装模作样。
晏翊没有回答,而是拿出帕子不紧不慢地拭着唇角。
不论她那番说词是真是假,但至少经了今日一出,她定能清楚的认知到,那赵凌护不住她,她若想安稳活着,便在他面前将这戏演到他厌倦为止。
晏翊的厌倦代表着什么,宋知蕙比任何人都心知肚明,待她在晏翊面前失了用处那一日,定是她的死期。
宋知蕙也拿出帕子擦唇,含笑着再次谢恩。
下山时,宋知蕙腿肚子开始打软,只下了几层便扶着一旁树干面露难色。
晏翊却是上前俯身,直接将她横抱起身,腾空那一瞬,宋知蕙低呼了一声,手臂下意识便环在了晏翊的脖颈上。
“王爷……”
“孤可没空再与你耗。”
下山这一路,她都是在他怀中,从最开始提心吊胆,生怕晏翊忽然哪根筋不对,将她直接摔下山去,到后来那困意慢慢袭来,她逐渐意识涣散,最终不知不自觉合了眼。
再次睁开时,她已坐在马车中,眼看马车便要驶入城中。
宋知蕙意识到自己睡了许久,连忙从晏翊怀中起身,她侧过身整理妆容,身后传来晏翊不冷不淡的声音,“皇上忌惮幽州兵力,你觉得当如何?”
那慌乱的身影略微一顿,然随后便故作镇定地回话道:“广阳侯年已过百,早不是当打之年,赵凌也尚未弱冠,广阳侯短时间内不会交权于他,妾以为幽州暂不为惧。”
“暂?”晏翊抓了重点。
宋知蕙因背对晏翊,此刻那幽冷眼神便没有让他看到,她缓缓吸了口气,握着拳道:“幽州将士常年驻守边关,包围大东安宁,广阳侯屡立战功,更是为大东建国功臣,若圣上难以容他,岂不是叫所有将士心寒,若忠臣不敢再尽忠,那周而复始的王朝兴衰便是……”
“杨心仪。”晏翊冷声将她话音打断。
宋知蕙咽下喉中咸腥,装作整理额前乱发的时候,抹去了眼角的湿润。
在方才那席话中,她说的是广阳侯,想到的却是杨家。
晏翊如何听不出,他默了片刻,略缓了一丝语调,“杨歙教你的治国论,看来是白教了,身为帝王,合该权衡势力,你不知吗?”
宋知蕙缓缓转过身来,脸上已看不出半分异样,平静分析道:“王爷所言极是,幽州此刻无战,那数万大军的确该被朝内忌惮,但圣上重任君之名,便不能贸然对幽州出手,妾觉得应先解决世子婚事。”
“一个女人罢了。”晏翊冷嗤,“上过沙场之人,若真铁了心要做何事,便说是世子妃,便是那赵凌,都未必能让广阳侯在意。”
晏翊从一开始就对所谓赐婚觉得无用,当初能那乌恒之战时,他便打算直接将那父子二人除去,可到底还是因这身份原因,他无法亲自出面,让那半死不活的赵凌被广阳侯生生救了回去。
想到此,晏翊眸中那冷然的杀气便倏然生出。
宋知蕙莫名打了个寒颤,不敢再轻易开口。
须臾,马车停在广阳侯府门前。
还未下车,便听外间传来朗笑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