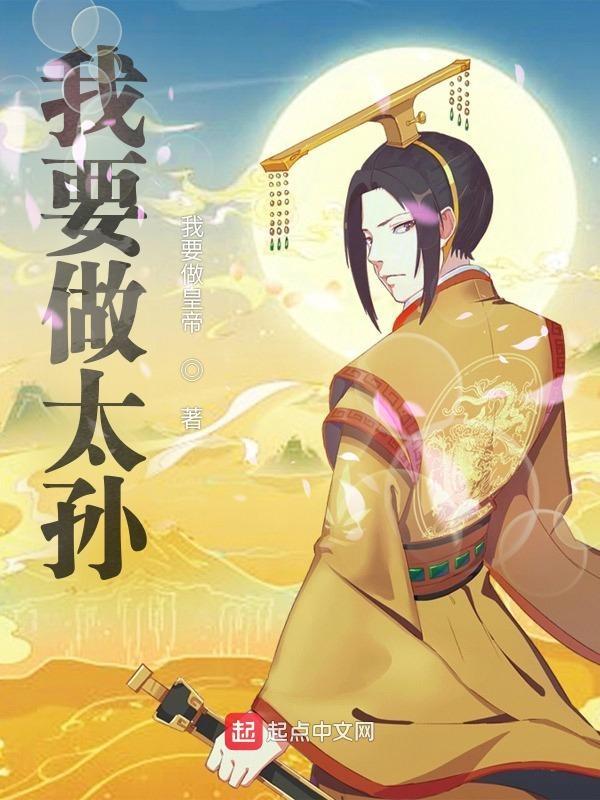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陷落春日 > 2030(第7页)
2030(第7页)
她抿了抿湿润的唇,晶亮的色泽太过耀眼,谢辞序盯着她红肿的唇瓣,很轻地吞咽了下喉结,而后移开。
他今日似乎分外严苛,并不接受这样的指代,眉梢挑起,还在执着于她的回答。
岑稚许偏不如他意,吸了吸鼻子,作势要缠在指尖的领带取下来。只可惜刚才的吻太激烈,原本系得规整的温莎结也被扯得没了形,松散地垂在他颈侧,更显得凸棱的喉结禁欲而性感。
她先前光顾着撩拨谢辞序了,又被他急促而凶猛的吻罩住,直到此刻才后知后觉般发现指端被勒得发红,轻轻一碰便针扎似的疼。
据说人在濒临窒息之际,大脑皮层也会迸生出快感,同性。爱迭至高潮时分极为相似。岑稚许每次刷到类似的东西,都是皱着眉头看完的,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喜好。
现在却好像理解了一点。否则,又该怎么解释,她会蠢笨到手指充血都未有所察。
“你下次……能不能轻一点。”岑稚许怪怨他。
好在发红的指尖被释放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颜色,除了皮肤表面被领带的面料磨得有些疼以外,并没有别的感觉。
莫名其妙背了一口黑锅的谢辞序将她的手揉进掌心,紧蹙高挺的眉骨微动。
“接吻的时候,手不要到处乱放。”
岑稚许听完不高兴了,“我牵你领带,只是想跟你近距离说话,哪里知道你会吻我。”
谢辞序并未为此而道歉,在某些事上可以理智,意乱情迷之际,酒精尚且不足让人失去该有的判断力。
她身上似乎哪里都碰不得。嘴唇吻过会泛出浅淡的绯,腕心稍作用力也会留下印记,连腰肢也敏感得不行,他想发狠地掐紧她的腰,让她纤薄的腰线严丝合缝地同他贴紧,却又怕稍不注意弄伤了她。谁曾想,连她主动勾缠着他的领带,借着这样的力道支撑,也能搞成这样。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谢辞序情绪足够稳定,哪怕她这通怪罪实在是太过骄纵。
他全盘接受她的坏心思,岑稚许当然不会客气,用含糊的音色诚恳地跟他描述:“还好,就是刚才被勒得有点发胀,觉得不太适应,现在习惯了倒是没什么感觉了。”
她自顾自地形容着,表情带着绘声绘色的意味,试图让谢辞序也对那种涨疼的感觉感同身受。
岑稚许呼出的气息裹挟着他唇腔里的浅淡酒香,如细腻温软的香风渡过来,搅得谢辞序浑身发躁,扯松领口的钮扣,“那就好。”
见谢辞序睨过来的眼神带着欲言又止,哪怕他表面依旧云淡风轻,仿佛下一秒还能同人谈笑风生,可那双眸子里充满了占有欲的进犯,她几乎是在触及的一瞬间。
便明白过来。
他也会有所反应。
并且不比她少。
涨得……发疼吗?
岑稚许脸颊陡然攀升出一抹热意,眼前不合时宜地闪过在他房间里看到的画面。结实劲猛的腰腹,极具爆发力的年轻身体,以及超出认知的内裤尺寸,接吻时充满掠夺性,种种因素累迭,思想一旦脱缰,便朝着不可抑制的方向飞速发展。
他在床上,应该很厉害。
哪怕什么技巧都不懂,凭着上天赏饭吃的本事,也不容小觑。
想到这里,岑稚许脸颊微微发热,调转话锋,“辞哥吃饭了吗?”
谢辞序喑哑地“嗯”了一声,喉结沉力,“你没吃?”
“刘教授研究室的一台除尘设备坏了,我和厂家的工程师在那研究了半天。”
谢辞序:“你也上手修了?”
“我主要负责在旁边偷师。”
清淡的一声笑从鼻息里溢出来,谢辞序迎上她骄傲的视线,低冽的眉眼也感染上几分笑意,揽紧了她的肩,“想吃什么?中餐,还是别的。上次我看你对西餐的兴致似乎不高。”
不是兴致不高,是菜品样式真的不够惊艳。能够评得上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必然有出彩的地方,只不过岑稚许也是精娇玉养长大的,看过、尝过的好东西太多,中规中矩的便很难再博她一笑。
岑稚许也学会了他的惜字如金,“随便。”
反正难办的又不是她?不是吗。
这个点正是用餐的高峰期,好的餐厅都需要提前预约,也有专门为谢家留有一间包厢从不待客的,只是过去的路太堵,花费那么长时间,太不划算。
谢辞序想到了一家园林式中餐,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在闹市中难得几分雅致的情调。
岑稚许没有意见,确定目的地后,装模作样地说自己腿软,谢辞序终于凝神瞧她。
大概是今天同他见面也算一时兴起,并没有刻意打扮过,驼色开衫里头是件平领吊带,细白的长腿被短裤盖住,这样的穿搭在大学城附近比比皆是,但她沙丘般婀娜的身形实在饱满,将同样露肤度的衣服,平添了勾人的懒倦。
人间富贵花,用来形容她竟也恰当。
“好好的,怎么会腿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