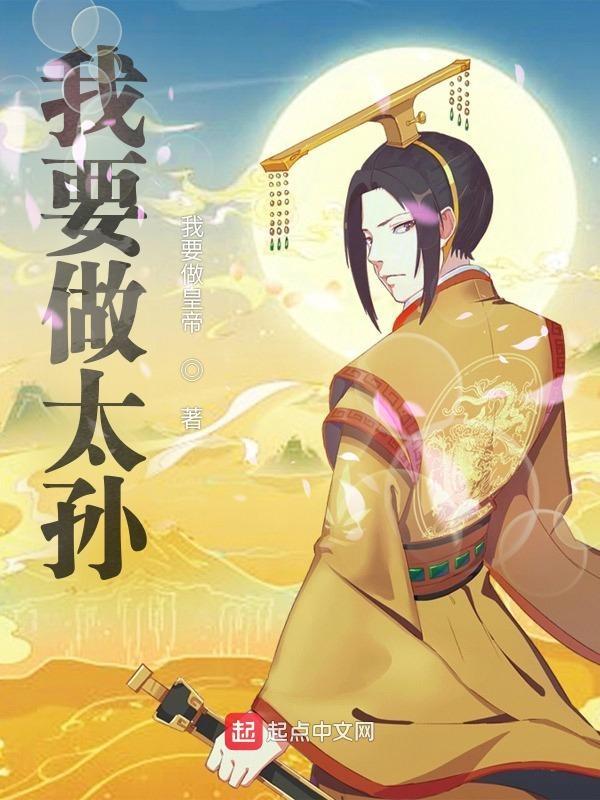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我,恶女,只想造反 > 4050(第35页)
4050(第35页)
提及吕家,柳司齐是又惧又怕,想说什么,终是止住了。
王学华精明,从中看出了端倪,把这茬儿记下了。
另一边的吕家已经接到衙门传来的消息。
吕公致德高望重,怀安郡太守虞茂辉还是他的门生,往日甭管遇到何人下来,他们都能很好应付,唯独陈九娘是个棘手货。
她的大名在这些官绅耳里简直臭名昭著,无人不厌恨。如今查到柳家,私盐一事定然瞒不住了。
长子吕德旭忧心忡忡,因为这些日吕公致在病中,不宜为琐事劳神。他怕柳家人的嘴不紧,命人盯着衙门的动静,必要之下灭口也使得。
当天傍晚北门街的玉器铺被查封,入夜时分宋青等人把衙门封锁起来,相干人等禁止随意出行。
孔县丞被留在衙门,眼皮子狂跳不已。他强忍着内心的不安,试探问宋青道:“这位军爷,不知衙门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何故这般大动干戈?”
宋青道:“好端端的九娘子自不会为难你们,定是有什么事牵连了进来。”顿了顿,“倘若孔县丞是清白的,九娘子自不会乱定你的罪。”
孔县丞忙道:“不敢不敢,九娘子该查的也查了,我等实在……”
宋青:“隔壁盛县平安无事,想来你们长姑县,也能有好运气。”
孔县丞闭了嘴。
相较于他的恐慌,温县令倒是淡定许多,因为陈皎差人搜查衙门的家属院,并未搜出什么来。
按照古氏的说法,玉器铺是走温县令的门路,花高价买玉器字画,变相贿赂,那得来的那些钱财呢,又藏在何处?
官兵们把衙门和温县令的别院翻了个底儿朝天,连个铜板都没见到。
陈皎跟马春讨论此事,马春道:“会不会寄存到别处了?”
陈皎摇头。
一般来说,贪污来的钱款如果通过家眷寄存到别处,一旦被查,很容易顺藤摸瓜挖出来。
看温县令无比镇定的样子,想来掩藏得很好,再加之衙门里的账目也处理得老道,可见他们早就做好准备应付这起清查。
陈皎审问温家的仆人,平时温县令的喜好。仆人说他喜爱字画之物,并且平素生活节俭。
这点陈皎是认可的,不管是不是装,温家人的衣着都很寻常,非常低调。
但钱呢,藏到哪里去了?
陈皎自知审问不出什么来,倒也没有为难温县令,他若吐露钱财之处,那便是自证受贿。
温县令被停职调查,理由是柳家告发他受贿。
对此温县令并未替自己辩解什么,文远和审问,他死口咬定自己冤枉,也跟柳司齐一样嘴硬。
陈皎受不了那种泰然,索性把他下了狱。
途中王学华同她说起古氏跟柳司齐的争执,提及吕家。
陈皎的心思活络了,让宋青他们查柳家私盐的来路,定然跟吕家脱不了干系。
因为柳家仅仅只是普通的商户,想要接触私盐渠道,肯定需要门路,他们这般惧怕吕士绅,或许是条线索。
陈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查,不曾想捅了马蜂窝。
她亲自把温县令送到牢里,温县令还是那副死样,镇定自若。
陈皎刻薄道:“这些日就委屈温县令了,当初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把周宝雨等人抓来,现在算是一报还一报。”
这话触动了温县令的心弦,忍不住道:“九娘子滥用私权,就不怕报应吗?”
陈皎愣了愣,“报应?”当即便笑了起来,肆无忌惮道,“不妨告诉你们,我陈九娘就是官绅的报应。”
温县令盯着她,没有吭声。
陈皎继续道:“盛县毫发无损,温县令且好生想一想,为何他们能躲过我这个瘟神的清查。”
温县令皱眉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温某无话可说。”
他这般嘴硬,令陈皎懊恼,指了指他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总能抓到你的把柄。”
温县令不想跟她费口舌,闭目不语,陈皎甩袖而去。
角落里一直竖起耳朵听他们谈话的女人似乎嗅到了脱身的机会,在陈皎等人路过时,忽地开口,“陈九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