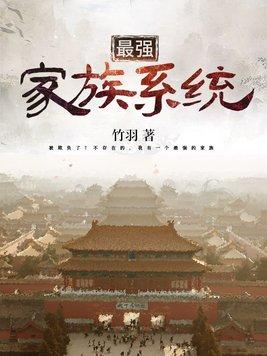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承平年少 > 80100(第9页)
80100(第9页)
齐姑姑吩咐宫人把银匣子收拾起来,又张罗着梳洗的巾栉,一面扶着宝珠起身,劝慰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夫人还请放宽心,眼下好好养伤最要紧,奴婢草芥之人,哪配夫人费神呢?”
她说的也在理。宝珠后知后觉,身边这些人的去留,将来自会有皇帝作主,哪用得着她咸吃萝卜淡操心?
如此再好不过。他是明君,再气再恨,极少迁怒不相干的人。宝珠唇边不觉绽出一点笑意,昙花一现,只有她自己能察觉。
是非名利以外,她是多么爱恋他。
洗去一路的尘埃,换了家常衣裳,齐姑姑扶着宝珠在美人榻里卧下,喂她用些汤,杏儿则替她除了绸袜,取来白玉滚轮轻轻舒缓足周的经络,一面笑道:“夫人且瞧吧,等这些淤青散尽了,咱们还能养得比羊脂玉都润白。”
宝珠笑了笑,正要说话,听说秋月回来了,还代门上递话,云姨娘求见。
想是为文歆的事。宝珠点点头:“请她进来吧。”
云栀进门来,盈盈拜了一礼,道:“适才王御医来瞧过,说歆儿多半是吓着了,一应药都不必开,叫照料他的傅母们细心护着些就是。我又托他开了剂壮骨生肌的药,内服外敷都使得,姐姐看看可妥当?”
宝珠微一抿嘴:“难为你想着。”示意齐姑姑接了,又不禁叹了口气,道:“玉桃不在了,身后这一摊子事都须得你料理,少不得要焦头烂额一阵,文歆那里,又没法儿真一股脑儿全撂给奶娘婆子们…”
玉壶倒闲着,可惜是个不肯揽事儿的,白得个大胖小子固然好,可毕竟是隔了层肚皮的,往后但凡有一点差池,谁能说得清?又不是自己不能生。
云栀则不一样。宝珠一听她这声口便知,她是样样都要强,不过囿于身份,正经主子没发话,到底不便自说自话、跳得太高。
然则自己既不管事儿,就不该擅作主张,轻易允诺她。宝珠话锋一转,又问:“侯爷的意思呢?”
傅横舟的意思?不提还罢,一提云栀便暗暗齿冷:他真以为,那一位厌弃了的女人,他就能凑上去嘘寒问暖、聊慰芳心?
他居然想把孩子给宝珠养!
87。八十七驱邪香囊
为着这一回宝珠伴驾出行,有的人又坐不住了。三月初九宝珠进宫那天,云栀又见着了那张令她厌烦的脸,阴沉着问她还想不想替父兄翻案。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连自己男人的笼络不住的主儿,还在她面前夸什么海口逞什么威风?
云栀面上不得不敷衍,心里却丝毫不指望这纸老虎。与其受人辖制去构陷宝珠,倒不如,取宝珠而代之。
王春平在偌大京城里是何等地位,也不辞辛劳甘愿为其驱使——这种呼风唤雨的滋味,谁能拒绝?
眼下宝珠暂且失了那一位的欢心,云栀想要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便了,索性另辟蹊径,把侯府唯一的孩子养住了,借此央傅横舟替自己讨个身份来,效仿薛光禄家那位贺夫人一般,今后也好在场面上行走。
听见宝珠把事情推给傅横舟,云栀脸上也不作恼色,抽了手帕出来,按一按眼角,哽咽道:“有一句话,我连在侯爷跟前都不敢说,只因为姐姐是菩萨心肠,又同为女人,不妨与姐姐透个底儿罢了…”
宝珠不作声,专听她怎么说:“姐姐是最尊贵不过的人儿,玉壶姐姐亦是清清白白的出身,只有我——当日容我进府来,瞒了老夫人,是怕她老人家动气伤身,然而我自己,又有哪一日忘却得了自己是何等卑贱不堪,自小在那肮脏地方受尽折磨,得蒙侯爷垂怜,是老天爷瞧我这辈子太苦,发了莫大的善心,但要报他错爱之恩,为他开枝散叶,却是…痴心妄想了!”
说到伤心处,她已是泣不成声。宝珠眼睁睁看着,究竟有两分不落忍,软语温言道:“既是爱你怜你,侯爷又怎会不懂你的苦处呢?”
这话实则亦触动了自己的心事,忍不住顿了顿,宝珠方才又道:“我是个一问三不知的闲人,以己度人,怕文歆交给你,越添负担,既然你自己情愿,那自然皆大欢喜。不妨觑空请侯爷来,他必会体谅的。”
玉桃毕竟是偏房,身后事再郑重也有限,宝珠本想等午饭后择个机会见傅横舟,不想正和云栀说话间,傅横舟自己来了。
“昨日正好得了一批上佳的梅花冰片,便托人配了些三花接骨散。”傅横舟道:“夫人的脚伤耽搁不得,还是尽早安养才好。”
宝珠心里暗笑:枉她自以为掩藏得很好,原来这一个个都已将她的行迹一览无余。
“多谢侯爷盛情。”仍旧是不远不近的一句道谢,宝珠这会儿不再歪在榻上,隔着珠帘依旧正襟危坐起来,又见秋月捧了剔红云纹盏托来,便向云栀道:“我脚下不便,妹妹代我为侯爷奉茶吧。”
云栀会意,应声从她跟前退出,到帘外红木嵌螺钿圆桌前坐下,秋月又奉一盏茶与她。
宝珠便问:“侯爷从哪儿过来的?”
傅横舟道:“去送了王御医一回,又瞧了瞧歆儿,这会儿他倒安稳了。”
宝珠感慨一时:“稚子柔弱,倘无慈母矜育庇护,何以长成?”她望了云栀一眼:“我虽有心,却实在力有不逮;云栀呢,心心念念盼着有个孩子作伴,哪怕再忙也不觉得辛苦,一位母亲待儿女的心,大抵都是这样吧?若真能如此安排,还望侯爷能多加关怀,叫他俩成为彼此的依靠吧。”
这话说得情真意切,反倒叫傅横舟有些不解:那么她呢?她缘何不为自己谋划呢?想是这个孩子可以成为云栀的依靠,却无法成为她的依靠——她依然念着那个势位至尊的人,情理之中。
沉吟片刻,他说:“一切依夫人的意思。”
语调里仿佛有幽怨之感。宝珠听了尚不以为意,云栀则是洞若观火,因为早不将他视作良人,故此略觉不忿,失落得有限。
这二人不过是她的过墙云梯,且由他们安乐些时日,待她扶摇直上,还何须介怀?
她站起身福了福:“妾过来得有些时候了,只怕底下当差的人有事要寻,侯爷夫人高坐,妾先告退了。”
傅横舟点点头,继续坐着没动。
宝珠心里便不大受用。若是在花园里,天高地阔的,两人相对着一时半刻还罢了,如今傅横舟杵在她的房里,多少就有些不速之客的突兀,且她的脚踝还没好全,端坐久了,难免觉得累。
便示意秋月添了一回茶,说:“昔人已去,侯爷伤心之余,也别忘了保重自身。”令齐姑姑去取两盒阿胶膏来,说道:“之前路过烟台时买了些,总是物离乡贵,实际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侯爷只当作一份土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