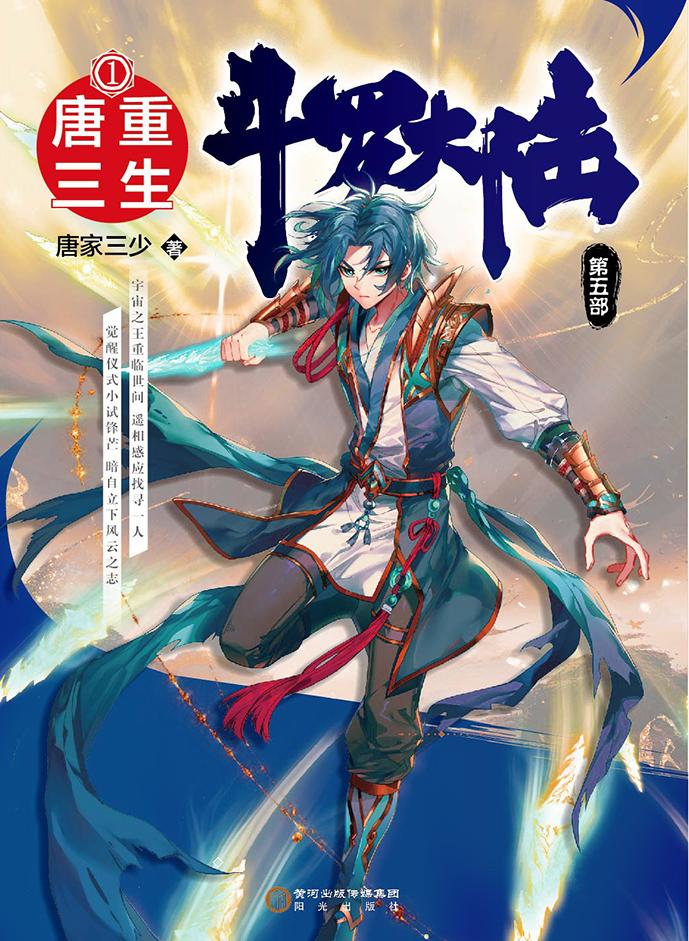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承平年少 > 6080(第9页)
6080(第9页)
宝珠看了她一眼,片刻也只点点头,转身回到屋中,又说:“将那份文契寻出来收好,索性明儿就去把人接了,一道好安置些。”
她指的是傅横舟倾心的那名妓子,唤作云栀的。
齐姑姑应了个“是”,杏儿听着却暗自奇怪:成婚不到一日,怎么就添进来这许多人了?是靖宁侯待宝珠不好吗?
她本合计着等齐姑姑走了,要问一问宝珠,说一说体己话。可直到该就寝的时候,她老人家仍岿然不动地守在屋中,还打发杏儿秋月两个回自己房去。
缘故也是明摆着的:她们两个未嫁的女孩儿家,又不是要做通房的,留下来知道怎么伺候吗?
两个人只好一块儿出来,没走两步,远远见着一道气宇轩昂的身影——居然是皇帝。
她俩慌忙行下礼去,等皇帝走过来,杏儿犹忍不住问:“您怎么来了?”
皇帝随意一抬手,免了她俩的礼,却不搭言,只瞥了杏儿一眼,嫌她问蠢话。
负着手迤迤迈上台阶,推门进去,宝珠正坐在妆台前,发髻全拆了,由齐姑姑给她通头发。
见皇帝进来,齐姑姑搁下梳子,蹲了个福,便收拾起物什退出去了。
宝珠披散着乌发,行完礼,却皱起眉头,问道:“您怎么又来了?”
66。六十六山茶手脂
皇帝哑然失笑,反问道:“我怎么不能来?”
宝珠不吱声儿了。皇帝上前去抱着她,隐隐觉着一阵暖香袭来,不禁将头埋在她颈窝里,深嗅起来,一面喟叹着:“好香…”
炽热的鼻息缠绕在颈子上,宝珠被他闹得有点痒,避了两回,索性推开他:“是抹头发的香露。您喜欢闻,明儿带两罐回去。”
“算了。”皇帝摇摇头,拉着她一道坐下来:“人我都带不回去,带这些有的没的做什么?”
宝珠不接他这话茬,伸手放下玻璃镜的罩子,见台上一瓶山茶手脂没盖上盖儿,便取过来些,点在手上慢慢涂着。秋季里气候干,她皮肤又薄,不留神作养着,再过些日子就要生那种小细纹,像小的裂口似的,觉着怪难受。
一抬头,见皇帝眼睛瞬也不瞬地盯着自己瞧,宝珠便问:“您要涂些吗?”
皇帝喉头滚了一滚,说:“别涂了。再涂真没法儿好好坐着说话了。”
宝珠一顿:男人家就是有这么一样德性,一旦有了肌肤之亲,再相处起来总没个正经样儿了。
她垂下眼眸,说:“傅家的口味我不习惯,今儿一整日都没怎么吃东西。”
皇帝登时发起急来:“这是怎么说?”站起来就叫人去起灶做饭。齐姑姑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哪会这些?那些宫女儿们更不在话下。齐姑姑便提议说,有宫方配制的灵芝粉,这会儿调上一碗来,又便宜又落胃,不至于搁在腹中夜里不好安睡。
宝珠拦都拦不及,这时候方才插得上话:“大晚上的折腾什么?灵芝粉我也不要,没病没痛的喝它,怕补出两管鼻血来。”
好容易把人都给打发了,她回过头,对心有不甘的皇帝道:“这时辰勉强吃几口,哪有安生睡一觉管用?”
皇帝这才听出来,她拐弯抹角想说的是什么。却还嘴硬:“有我给你值夜呢,你只管睡就是。”
正是因为有他,才难得安生呢。
皇帝又说:“也是我疏忽,偏把这么要紧的一桩忘了——明儿拨两个厨上的来,依着你的口味单做就是了。”
宝珠听了,幽幽道:“您还真打算把这里当成行在了?”
皇帝不以为然:“什么行在?往后除了见大臣,这儿便是宣政殿。”
宝珠还欲说话,一时撑不住倦意,侧身掩口打了个呵欠。
皇帝便哄着她:“歇了吧。躺着松松筋骨,再说会儿话也是一样的。”
那可未必。转念又想:他明日又得不到五更便走呢。宝珠也就依他所言,被衾是早铺好熏暖了的,替他宽了衣,又要唤人准备洗漱的巾栉来,皇帝却说:“费那个工夫做什么?”
屋里的铜壶中还剩了小半温水,便就着宝珠的用具擦洗了一通,幸好青玉牙刷本是成对的,宝珠取了另一柄给他用。
一时拾掇完了,皇帝坐在床边,说:“我现在浑身都是你的味道。”
宝珠正理着床帐,闻声只乜了他一眼,让他睡到里面去。
皇帝不肯:“说好了我给你值夜的,你睡里面。”
无论是皇后还是妃嫔,有幸与皇帝同榻而眠时,都要睡在外侧,一则便于夜里伺候茶水之类的,二则若逢着意外变故,也能挡一时半刻,为亲卫护驾拖延时间。
宝珠却是从来睡在床里侧的。如今因为是在宫外,她怕禁卫不够森严,方才有这么一句。
皇帝可没想那么多,见她踟蹰,干脆拥着她一块儿倒下去,虽然答应了放过她一晚,但搂在怀里亲一亲总不能叫食言。
蹂''躏完了嘴唇,又轻吮着她脖颈上的那一小块儿伤痕,淡粉的颜色,比别处更娇嫩许多,触感像花瓣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