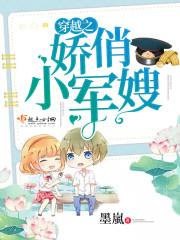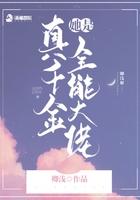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怎么看我都是个优雅绅士 > 8090(第29页)
8090(第29页)
就连雪莉最后出现的咖啡厅的内部监控,也一并被组织情报人员入侵并拷贝了回来。
只可惜,哪怕是尼昂仔细翻来覆去的查看,也没有在影像记录里找到任何行径可疑的人物,就连影像里雪莉本人的表现,也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不是蓄意绑架吗。
那么是无差别随机犯罪?
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一般罪犯很难有这样的底气,而雪莉也绝不是那种会被人三言两语骗到偏僻场所不谙世事的天真小孩。
能够在这种条件下成功强行挟持,怕不是有专门学习过如何避开眼线和制服他人的专业人士所为。
尼昂细长的眼睫投下的阴影模糊了眼底的思绪,不久,他关掉了手中没什么太大用处的监控录像。
日本的监控摄像头分布并不密集,至少直到18年的当下,例如地铁、电车之类的公共场所的车厢车站,都仍旧缺乏监控,甚至都没有安检——哪怕这些地方过去曾经发生过不少人为事故,也仍旧没有什么太多改变。
同理,人行道的监控安置也并非天衣无缝,除了一些人流量较大的特定场所,比如人来人往的大十字路口等等的监控设备密度会高一些,其他一般场所的监控与监控之间,往往会有一段空白间隔。
加上各种大街小巷,死角自然就格外的多,如果是对监控分布熟悉的人,甚至有一路躲避监控从一端抵达遥远另一端的可能。
很多沉案日本警方迟迟破解不了,也多少与这个有关。
监控不密集、有死角,而日本这个地方的文化也讲究与人保持距离,尤其是大城市,陌生人之间的人情味要淡很多,当然,这种状况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都或多或少出现趋同现象。总而言之,除非本身就奇装异服行为古怪,否则一般也很少会有目击者存在。
而缺少这些关键要素,就很容易导致一些寻人的案子陷入僵持。
就像是雪莉的这起事件一样——她被组织发现失踪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搜寻期。从监控上的时间来看,也很难判断对方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绑走的。
哪怕是尼昂,一时半会也很难所有进展。
主要是他仍旧被怀疑着,让他不得不分心处理自己的事。雪莉的珍贵性与其唐突消失的行为,让原本已经放下戒心的组织高层再度怀疑起了雪莉的忠心:诚然,尼昂说得对,雪莉对她的姐姐感情很深,不该会放弃复仇,做出独自逃离组织的事——组织是最能给她复仇力量的存在。但这一说辞的前提,是雪莉真的相信了是FBI害死的她姐姐。
……万一她认为组织没有保护好宫野明美,在危急时刻选择放弃了对方呢?
迁怒是最不讲理的,谁规定憎恨不会蔓延到其他人身上?如果雪莉也一并敌视起了组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因此看上去最有可能被雪莉利用的尼昂,哪怕说辞合理,也仍旧没法完全洗清高层对他的怀疑。
“我什么都没做。”
尼昂还是这个说法,也的确没有露出任何马脚。但与此同时,他也仍旧拒绝高层要求他“证实自己”,去搜寻以及灭口雪莉的命令。
然后适当给予“让步”地补充:
“如果你们执意要我插手,我可以去寻找、救援雪莉,却不会动手灭口,我还是那个判断:她不是自愿离开的。”
尼昂说辞沉稳笃定。
而依据他的态度与表现,内部不算太过团结的组织高层,也微妙分成了救援派和灭口派。
前者惦记着雪莉的研究成果,觉得如果对方没有背叛,还是再给人一个机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人救回来了,恐怕处境会直接触底反弹,迎来比以往都要更加可怕的监视。
而后者则认为组织安全第一,他们怀疑雪莉更甚于重视雪莉。
疑心病过重,让这一批人常年阴谋论:哪怕雪莉是被迫绑走的,那绑架者就不知道雪莉身份吗?如果雪莉禁不住审讯,主动说出了机密情报,为了生存而另外协助他人,那昔日他们惯用的剧毒就将会落到他们自己头上,曾经雪莉见过的组织成员,也将因此而面临暴露的风险。
疑心病,总会把事情往最糟糕的地方想,然后对此深信不疑。
尼昂是救援派。
微妙的,琴酒也站在了他那头,属于偏向救援派的人。
尼昂对此:“……你不站我对立面可还真罕见,看门犬居然选择不咬人了?”
“既然你判断雪莉不是主动离开,那救援自然是更好的选择。”
琴酒语气理所当然:
“她的研究水平的确是组织顶尖,就例如改良后的APTX4869,就的确相当好用,她能给组织带来巨大的利益——哪怕是研究的副成果,也有十足的价值,既然如此,她如果没有反心,我自然判断优先将人带回。”
尼昂:“APTX4869?什么东西?”
琴酒挑眉:“你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知道。”尼昂反问,“看你反应,估计是毒药吧?我虽然不排斥,但也说不上多么爱用毒。哪怕用,也很少用不熟悉的毒——太麻烦了,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否则还是枪更便利。”
琴酒低哼了一声,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药盒丢给了对方。
尼昂接住打开,里面是三粒红白胶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