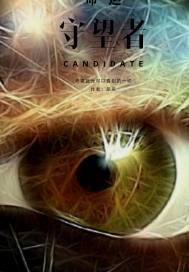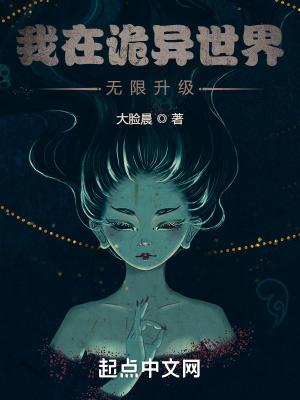第三小说网>秦始皇孙天界直播日常 > 23秦皇虎视苍生群汉武馀烈尚氛氲⑨(第2页)
23秦皇虎视苍生群汉武馀烈尚氛氲⑨(第2页)
“那可能是之前说的?”
“更扯了,之前说的等到今天才问?你当秦始皇和你一样记性不好脑子慢是不是?”
“你怎么骂人呢?”
“我……”
“够了!”争辩声才将将扩大了些,就被刘彻这一声镇住了。
刘彻实在没心思听他们吵吵,吼完就去戳嬴政头像:“是不是他背着我们悄悄地给你传授了什么预知未来之术?”
嬴政:“你想象力还挺丰富的。”嬴棠自己都不一定有那个能力,还传授。
“那你怎么知道的?”
“猜的。”这淮南王的封地明明和越临近,应当对越的具体形势比较了解才是,可他也持反对态度。这背后的原因还能是什么?不就是不想让中央介入他封地的事情吗?小心思这么多,要是一点谋反之心都没有,那才是怪事。
他没把自己的思路说出来,但刘彻把当时的情景回想了一遍,很快就明白过来他是怎么猜到的了。
思及此,刘彻对嬴政的欣赏又攀了一层:“不愧是始皇帝,抓造反都是一抓一个准……皇叔啊,你可干了件天大的蠢事,”他喃喃着,而后露出一抹微笑,“也过去挺久了,不知你坟头的草如今该多高了呢?”
他将刘安谋反的始末和嬴政说了一遍。
秦公子们对此表示——长见识了。
“可真是刘彻的好皇叔,大汉的好封王,他汉才建立多久,子孙们就变妖魔鬼怪了。”嬴政这话当然不是在嘲讽刘邦,毕竟就汉初那个情况,郡国并行制确不失为一道稳定局势良方。他是在点那些把血缘关系吹上天的人。
这会儿他们的血缘关系还没出五服,就闹成这样。若坐在皇位上的是个软骨头,恐怕早就被生吞活剥了。
曾支持分封制的朝臣们纷纷低下头。
武周时期。
武曌看向太平公主:“太平,就对越态度上,两个派别的争执,你怎么看?”
太平公主思忖了片刻:“女儿以为,这场争执,对汉武帝来说,并非是全然令人烦厌的。至少,他看到了一股新的可用力量。”
武曌微露笑容:“是什么?”
“就两次三公的撤换来看,汉武初时的朝堂势力,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是和窦太后一样推崇黄老之学的派系,代表人物就是庄青翟、许昌等人;二是支持汉武帝进行改革的儒学派,以窦婴、田蚡为首。但在这次事件中,明显可以看出,田蚡等人虽于内政上站了汉武帝,但在对外关系上,却是持保守态度的……汉武帝先前既然派遣了张骞出使西域,就证明他的雄心已不止于维持内部的安和。田蚡等人,注定不能为他长期所用。他需要一批,既效忠于他,又有进取之心臣子。所以……”
“所以,这次围绕越人之争而展开的廷诤让他发现了新的支持力量,既要依靠汉武帝,又能为边疆事务提供有效建议,”武曌终于笑开,“朕之儿女中,独太平类母。”
一批符合自己期望又忠于自己的臣子对每个皇帝而言都是迫切需求的。
在士族中,这样的人太少太少。因为他们最大的倚仗是自己的家族,没必要将所有宝都押在皇帝身上。庶族就不一样了。士族的存在注定了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单打独斗——资源就那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庶族要是上来了,那上头人能占用的不就少了?所以啊,你们这些家伙给我老老实实地在底下呆着吧
在这种情况下,庶族想要实现阶级跨越,就只能依靠皇帝。他们靠着皇帝的提拔上来了,想进一步升官发财、在朝中站稳位置,就要老老实实给皇帝办事,当好皇党,否则,一旦他们失去皇帝庇护,那虎视眈眈的士族,就会立刻把他们踹下去。
由此可见,还是得科举。朝堂上天子门生多了,不但办事效率高了,连作妖的人都少了。
不叫那群自以为是的士族看清现实,他们就永远学不会听话。
【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彻底掌控朝纲。自此,正式开启了他的雄主之路。我们接下来将从中央集权、开疆拓土两方面来阐述汉武帝的功绩。
先来说中央集权方面。窦太后死后,汉武帝找借口罢免了窦太后所任命的许昌、庄青翟的职位,改擢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在田蚡任相的期间,他和窦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后,因灌夫骂座一事,二人矛盾彻底激化。窦婴不久后被斩首,次年春,田蚡亦病重身亡。此后,汉武帝开始起用功臣外戚以外的官吏,并提升了御史大夫的地位,分走了相权,使得丞相对皇权的牵制作用大为缩小。】1
由于这篇所讲的主要是汉武帝,是以嬴棠就没有细致讲解窦田之争,只将事情的起因经过投放在了光屏上。
不管是已经知道窦田之争始末的后世人,还是才刚涨知识的前朝人,在看到这段历史时,都不免唏嘘了一把。
当中被讨论最多的就是遗诏真伪和田蚡之死了。